
田艺蘅,字子艺,贡生,官安徽休宁训导。博学善文,10岁时随父过采石,即景赋诗: “白玉楼成招太白,青山相对忆青莲。寥寥采石江头月,曾照仙人宫锦船。”田艺蘅为人高旷磊落,嗜酒任侠。罢官归杭后,愈益放诞不羁,朱衣白发,至老愈豪,常坐西湖花柳下,挟侍女具座待客酬唱。着有《大明同文集》、《田子艺集》、《留青日札》、《北新关志》及《煮泉小品》等杂着数十种。
○文徵明蔡羽等 黄佐欧大任 黎民表 柯维骐 王慎中屠应埈等 高叔嗣蔡汝楠 陈束任瀚 熊过 李开先 田汝成子艺蘅皇甫涍弟冲 汸濂 茅坤子维 谢榛卢柟 李攀龙梁有誉等王世贞 汪道昆 胡应麟 弟世懋 归有光子子慕 胡友信
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着。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徵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徵明官。徵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彭孙震孟,自有传。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CW、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号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馆》二集。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或谓其诗似李贺,羽曰:“吾诗求出魏、晋上,今乃为李贺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着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袁CW,字永之,七岁能诗。举嘉靖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累迁广西提学佥事。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CW独长揖。无何,谢病归。子尊尼;字鲁望,亦官山东提学副使,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璚,副都御史。淳受业徵明,以文行着,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天球以书,谷以画,皆继徵明表表吴中者也。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着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着。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长乐知县,以学行闻。正德中,佐举乡试第一。世宗嗣位,始成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又请修举新政,疏皆留中。寻省亲归,便道谒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守仁亦称其直谅。还朝,会出诸翰林为外僚,除江西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闻母病,引疾乞休,不俟报竟去,下巡抚林富逮问。富言佐诚有罪,第为亲受过,于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简宫僚,命以编修兼司谏,寻进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右谕德,擢南京国子祭酒。母忧除服,起少詹事。谒大学士夏言,与论河套事不合。会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礼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给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与左侍郎许成名竞进,至相诟詈;而佐及同官王用宾亦争觊望,惟恐或先之,宜皆止勿用。”言从中主之,遂皆赐罢。
佐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平生譔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着《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着云。欧大任,字桢伯,顺德人。由岁贡生历官南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终。黎民表,字惟敬,从化人,御史贯子也。举乡试,久不第,授翰林孔目,迁吏部司务。执政知其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供事内阁,加官至参议。
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高祖潜,翰林学士。父英,徽州知府。维骐举嘉靖二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维骐引掖靡倦。慨近世学者乐径易而惮积累,窃二氏之说以文其固陋也,作左右二铭,训学者务实。以辨心术、端趋向为实志,以存敬畏、密操履为实功,而其极则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为实用,作讲义二卷。《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着《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
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抚按监司时有论荐,不复起。隆庆初,廷臣复荐。所司以维骐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孙茂竹,海阳知县。茂竹子昶,副都御史,巡抚山西。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岁能诵诗,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埈、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忭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十二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毘陵。家居,问业者踵至。年五十一而终。李攀龙、王世贞后起,力排之,卒不能掩。攀龙,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也。慎中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
屠应埈,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书勋子也。举嘉靖五年进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谕德。
华察,字子潜,无锡人。应埈同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
陆铨,字选之,鄞人。嘉靖二年进士。与弟编修釴争大礼,并系诏狱,被杖,后官广西布政使。釴终山东提学副使,兄弟皆能文。
江以达,字子顺,贵溪人。嘉靖五年进士。累官福建提学佥事。
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赋》几万言,见者惊异。十八举于乡,第嘉靖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出为山西左参政,断疑狱十二事,人称为神。迁湖广按察使,卒官,年三十有七。
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及官吏部,与三原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艺相磨切。其为诗,清新婉约,虽为梦阳所知,不宗其说。陈束序其《苏门集》,谓有应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雄,体王、孟之清适,具高、岑之悲壮。王世贞则曰:“子业诗,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瘁婉笃,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为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汝楠,字子木。儿时随父南京,听祭酒湛若水讲学,辄有解悟。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从王慎中、唐顺之及叔嗣辈学为诗。寻进刑部员外郎,徙南京刑部。善皇甫涍兄弟,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廷议改归德州为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与说经。治民有惠政,既去,士民祠祀之。历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兵部右侍郎,从诸大僚祝厘西宫,世宗望见其貌寝,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几卒。
汝楠始好为诗,有重名。中年好经学,及官江西,与邹守一、罗洪先游,学益进,然诗由此不工去。
陈束,字约之,鄞人。生而聪慧绝伦,好读古书。会稽侍郎董官翰林时,闻束才,召视之。东垂髫而前,试词赋立就,遂字以女,携至京,文誉益起。嘉靖八年廷对,世宗亲擢罗洪先、程文德、杨名为一甲,而置唐顺之及束、任瀚于二甲,皆手批其卷。无何,考庶吉士,得胡经等二十人,以束及顺之、瀚曾奉御批,列经等首。座主张璁、霍韬以前此馆选悉改他曹,引嫌,亦议改,乃寝前令,束授礼部主事。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请徙近郊居民坟墓,束疏谏,不报。迁员外郎,改编修。
束出璁、韬门,不肯亲附。岁时上寿,望门投刺,辄驰马过之。为所恶,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治有声。稍迁福建参议,改河南提学副使。束故有呕血疾,会科试期近,试八郡之士,三月而毕,疾增剧,竟不起,年才三十有三。妻董,亦能诗,束卒未几亦卒,束竟无后。
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束与顺之辈厌而矫之。束早世,且藁多散逸,今所传《后冈集》,仅十之一二云。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屡迁考功郎中。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报,复自引还。给事中周来劾瀚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终世宗朝,中外屡荐,不复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抚刘思洁、曾省吾先后疏荐,优旨报闻而已。瀚少怀用世志,百家二氏之书,罔不搜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文亦高简。卒年九十三。
熊过,字叔仁,富顺人。瀚同年进士。累官祠祭郎中,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亦束同年进士。历官山东提学副使。乡试录文,旧多出学使者手,巡按御史叶经乞顺之文。高心憾,寓书京师友人言经纰缪。严嵩恶经,遂置之死。及后大计,诸御史谓经祸由高,乃斥归,于八子中,名最下。
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十年十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复普放生之仁,凡羁蹄钅杀羽禁在上林者,咸获纵释。顾使囹圄之徒久缠徽纆,衣冠之侣流窜穷荒,父子长离,魂魄永丧,此独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广皇仁,悉加宽宥。”忤旨,切责,停俸二月。屡迁祠祭郎中,广东佥事,谪知滁州。复擢贵州佥事,改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皆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岁当大比,预定诸生甲乙。比榜发,一如所定。
汝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归田后,般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着甚多,时推其博洽。子艺蘅,字子。十岁从父过采石,赋诗有警句。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作诗有才调,为人所称。
皇甫涍,字子安,长洲人。父录,弘治九年进士。任重庆知府。生四子,冲、涍、汸、濂。冲、汸同登嘉靖七年乡荐,明年,汸第进士。又三年,涍第进士。又十三年,濂亦第进士。而冲尚为举子。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
冲,字子浚,善骑射,好谈兵。遇南北内讧,譔《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凡数十万言。涍,初授工部主事,改礼部。历仪制员外郎,主客郎中。在仪制时,夏言为尚书,连疏请建储,皆涍起草,故言深知涍才。比简宫僚,遂用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言者论涍改官有私,谪广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迁浙江佥事。大计京官,以南曹事论罢,邑邑发病卒。涍沈静寡与,自负高俊,稍不当意,终日相对无一言。居官砥廉隅,然颇操切,多忤物,故数被谗谤云。
汸,字子循,七岁能诗。官工部主事,名动公卿,沾沾自喜,用是贬秩为黄州推官。屡迁南京稽勋郎中,再贬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擢云南佥事,以计典论黜。汸和易,近声色,好狎游。于兄弟中最老寿,年八十乃卒。
濂,字子约,初授工部主事,母丧除,起故官,典惜薪厂。贾人伪增数罔利,濂按其罪。贾人女为尚书文明妾,明召濂切责之。濂抗言曰:“公掌邦政,纵奸人干纪,又欲夺郎官法守邪?”明为敛容谢。大计,谪河南布政司理问,终兴化同知。
濂兄弟与黄鲁曾、省曾为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后,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凤翼、燕翼终举人。而献翼为太学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为雠家所杀。
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母忧,服阕,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佥事,辖府江道。坤雅好谈兵。瑶贼据鬼子诸砦,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总督应槚以问坤。坤曰:“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饷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雕剿。条入歼其魁,他部必袭,谋自全,此便计也。”槚善之,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砦,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横于里,为巡按庞尚鹏所劾,遂褫冠带。坤既废,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于万历二十九年。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着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少子维,字孝若,能诗,与同郡臧懋循、吴稼竳、吴梦阳,并称四子。尝诣阙上书,希得召见,陈当世大事,不报。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经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卢柟,字少楩,浚县人。家素封,输赀为国学生。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跅驰,好使酒骂座。常为具召邑令,日晏不至,柟大怒,彻席灭炬而卧。令至,柟已大醉,不具宾主礼。会柟役夫被榜,他日墙压死,令即捕柟,论死,系狱,破其家。里中儿为狱卒,恨柟,笞之数百,谋以土囊压杀之,为他卒救解。柟居狱中,益读所携书,作《幽鞫》、《放招》二赋,词旨沈郁。
谢榛入京师,见诸贵人,泣诉其冤状曰:“生有一卢柟不能救,乃从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陆光祖迁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狱。柟出,走谒榛。榛方客赵康王所,王立召见柟,礼为上宾。诸宗人以王故争客柟,柟酒酣骂座如故。及光祖为南京礼部郎,柟往访之,遍游吴会无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乡人殷学为巡抚,檄令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会其地数震,攀龙心悸,念母思归,遂谢病。故事,外官谢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便,特予告归。予告者,例得再起。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独故交殷、许辈过从靡间。时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满,二人闻之,交相得也。归田将十年,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龙至是摧亢为和,宾客亦稍稍进。。无何,奔母丧归,哀毁得疾,疾少间,一日心痛卒。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自号沧溟。
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皆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有誉除刑部主事,居三年,以念母告归,杜门读书。大吏至,辞不见。卒年三十六。
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谢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臣守西门,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曰:“我在,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之。寻迁提学副使,卒官,士民皆哭。
徐中行,字子舆,长兴人。美姿容,善饮酒。由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汀州知府。广东贼萧五来犯,御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击之,让功甫宰,甫宰得优擢。寻以父忧归,补汝宁,坐大计,贬长芦盐运判官。行湖广佥事,掩捕湖盗柯彩凤,得其积贮,活饥民万余。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万历六年卒官。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由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调归德,居二岁弃去。嵩败,起建宁同知,累迁河南左参政,大计罢归。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泺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庆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籓不得出城,而讠寿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阴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浚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火煃、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余曰德,字德甫,张佳胤,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世贞诗所谓“吾党有三甫”也。魏裳,字顺甫,与曰德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曰德终福建副使,裳终济南知府。九一,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终巡抚宁夏佥都御史。佳胤自有传。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筑室山中,构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撰着。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着《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
世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即遭父忧。父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先世贞三年卒。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
世贞子士骐,字冏伯,举乡试第一,登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卒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举万历十九年乡试,再被放,即屏居江村,与无锡高攀龙最善。其殁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请于朝,赠翰林待诏。
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
友信,字成之,隆庆二年进士。授顺德知县。岁赋率奸胥揽输,稍以所入啖长吏,谓之月钱。友信与民约,岁为三限,多寡皆自输,不取赢,闾里无妄费,而公赋以充。海寇窃发,官军往讨,民间驿骚。部内乌洲、大洲,贼所巢穴,诸恶少为贼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诛其魁,余党解散。乡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贼,贼不敢发。岁大凶,民饥死无敢为恶者。
初,友信虑民轻法,涖以严,后令行禁止,更为宽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县如家,弊修堕举,学校城池,咸为更新。督课邑子弟,教化兴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
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明代文献中记载的玉蜀黍
原着:千叶德尔
翻译:于景让教授(科学农业 1973: 21卷5/6期)
承科学农业社社长康有德教授慨允转载
译者说明
哥仑布发见新大陆是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二行关於玉蜀黍的记载,并有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很奇特的玉蜀黍的图。『本草纲目』,据译者所知最早者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金陵胡承龙的刊本。李时珍是卒於1596年。据 Bratschneider,则本草纲目的出版年度是1560~70,自哥仑布发见新大陆至『本草纲目』第一版(1596)刊印,中距40年或不到80年。李时珍记录玉蜀黍,大概不会是在玉蜀黍传入的当年,自记录至刊印,中间亦有一段时期。故据『本草纲目』,则自哥仑布发见新大陆至玉蜀黍传入中国的湖北省,其间大概不到100或不到80年。
田艺蘅的『留青日扎』,是刊印於明万历元年(1573)。其中记载玉蜀黍是较本草纲目为详细。自哥仑布发见新大陆至『留青日扎』刊印,其间距离是81年。田艺蘅大概亦不会在玉蜀黍传入当年便行记录,而自记录至刊印亦经一相当长的时期,故自哥仑布发见新大陆至玉蜀黍传入浙江杭州,一定是远少於80年。
其间虽有葡萄牙人东航,而玉蜀黍传布中国各地的期间实嫌短促。
译者读过方志,而没有时间作大规模的搜索,亦没有想到从云南的方志读起,并且读线装书搜索资料,真如披沙淘金,往往费力极多而不一定有效果。故译者对於玉蜀黍传入中国的知识,是止於『本草纲目』与『留青日扎』二书,而疑问始终不解。
读千叶教授文,深惊其引用资料范围之广,而玉蜀黍有Persian Type, Aegean Type, Caribbean Type 之分,在我这一个读过农学的人,亦是最新的知识。读千叶教授文後,我的疑问,已大部份消失。试为译出,以供有同样疑问者参考。
据千叶教授给我的信,他不读农,亦不会中国话,真使我这一个读过农、会说中国话的人愧汗而无地自容。
京都大滨田稔教授先赐赠复印本,爱知大学千叶教授赐赠抽印本及参考资料,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图书馆允准任意翻阅方志及其他参考书,谨此一并致谢。
正文
|
一、 |
田艺蘅的『留青日扎』,到现在为止,一般皆以为是中国记载玉蜀黍的最古的文献**。
万国鼎编:五谷史话(1961)。
『留青日扎』刊於明万历元年(1573),(比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早五年。)『留青日扎』记载玉蜀黍是称御麦,文曰: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秆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得此种,多有种之者,吾乡以麦为一熟。古称小麦忌戍,大麦忌子,皆忌水也,故吴乡低田不可种。(于按:据中央图书馆藏隆庆六年刊本第二六卷校正)。
番麦之名,大概是如『本草纲目』所说,因传自西番之故。西番麦之名亦见於嘉靖三九年(1560)刊的平凉府志,而现今福建省的一部分亦是称玉蜀黍曰西番麦**。故吾人对於西番麦,可视为在中国古时尝流行於各地(于按:今江南一带仍称番麦)。
厦门称番大麦,浙江南部称番黍(据『五谷史话』)。
玉蜀黍自西部路线传入中国之说,虽为De Candolle所否定,而在现今的中国的农学者间仍为一有力的通说**,根据大约就在此项古时的记载。
汤起麟:玉米,p.1. (1956)
『留青日扎』说番麦是旧名,今称御麦,亦很值得注意。这一发音,自18世纪以来,尝普及於四川云南。万历四年(1576)的云南通志所载的玉麦,与玉蜀黍通称的御麦,是同音异字。元代末贾铭的『饮食须知』,也有玉蜀黍即番麦之名**。
如贾铭已知有玉蜀黍,则是在哥仑布发见美洲以前,中国已有玉蜀黍。『饮食须知』中,亦记有落花生:L. C. Goodrich 谓皆系後世所附加。(L. C. Goodrich,Early notic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Monumenta Serica, Vol.II,No.2,1937) 。天野元之助亦表示赞成之意。(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p. 54,1962)但就。『饮食须知』的记载方式以言,落花生是一新的项目,而玉蜀黍是附记在蜀黍项的末尾。故对於玉蜀黍或可视为蜀黍的一个品种。这不一定是指自西欧传入的玉蜀黍。故因落花生是後代附加,而类推玉蜀黍亦是如此,不一定是很适切的。
所谓御麦,是因尝供皇帝进食得名。故田艺蘅贾铭皆加以记载**。
参阅『五谷史话』。但笔者参考的东洋文库藏本学海类编中的『饮食须知』无御麦云云,故这或许是『谷谱』的记载,而误以为『饮食须知』的记载。谷谱曰:玉蜀黍一名玉高梁,一名御麦。因会经供御用,故名御麦。出西番。旧名番麦。(于按:谷谱文是由日文译出,手头无谷谱,故未能与原文对照)。
但是,是什麽时候、那一位皇帝吃过,则皆无说明。万国鼎氏的五谷史话,谓:御麦是好麦之意,是元代皇室的司膳者所用之上等的麦,故与玉蜀黍是不同的麦。但笔者另有意见,笔者以为这是把玉蜀黍与薏苡(Coix)混淆後所产生的传说**。
河南省郏县志气顺治年间,在「玉麦即玉蜀黍」下注曰:「即光武所饭之麦」。光武帝是东汉第一代皇帝,早期流寓於河南河北。尝有有人进献这个麦的传说,大概流传颇广。这大概是由伏波将军马援在南方食薏苡以为美持归献给光武帝这一事实所递演而成的传说。玉麦或御麦的形态,与薏苡者是比较近似的。如再稍逞想像,则与薏苡形态近似的玉蜀黍应当是波斯型。(于注:对於作者的这一个注,我表示怀疑。光武所食麦饭,据我的了解,是大麦饭。郏县志的注,已是附会,而作者的说明,似附会更多。)
田艺蘅的家乡是浙江省钱塘县,该处的玉蜀黍,干叶皆似稷,即皆似蜀黍(高梁)(于按:稷是现今所谓的粟,但在中国文献中误以稷为高梁,由来已久,说见拙作「黍稷粟梁与高梁」)。玉蜀黍与蜀黍,在幼苗时期,虽是专门家,亦不易监别。成长後,玉蜀黍中,有叶伸展作左右对称形,茎叶粗刚作深绿色者,这与比较上是淡绿色而有纤细之感的蜀黍,就可以区别了。葡萄牙人携入日本的Caribbean型的玉蜀黍品种,明治以後传入日本北部的北美型的玉蜀黍,该项形态甚为显着。在形态上,到最後为止,仍与蜀黍不易办别的玉蜀黍品种,是波斯型。一般以为这是亚洲特产的很原始的一型**。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田艺蘅喜爱农村生活,是十分了解农业的人物,故对於蜀黍与玉蜀黍的区别,应当是知道的。如是,则因波斯型的玉蜀黍是沿着波斯──希马拉耶──爪哇山系而分布**,故田艺蘅乡里的玉蜀黍是西方传来的品种,此种可能性极大,其记载云须如红绒,故其花柱大概在抽出时就是红色。
S. Nakao 1958 Transmittence of cultivated plants through the Sino-Himalayan route,in H Kihara (ed.) Peoples of Nepal Himalaya. p. 397~420, Kyoto.
云南省蒙北县称曰红须麦的植物,据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指玉蜀黍。故在中国的西南地区确实是有着该项种类。江苏省娄县志称玉蜀黍曰鸡头粟。故在长江下游的平野中,可视为与田艺蘅的乡里相同,亦具有很多红须的品种。
田艺蘅尚附记一很重要的事项。他故乡的钱塘江下游地方,是水田植稻的地带,植麦甚少,故如玉蜀黍似的夏季作物,纵令传入,其扩大裁培的可能性是很少的。故田氏故乡的钱塘县,邻接於『饮食须知』作者贾铭的故乡的海宁县及李时珍家乡的湖北蕲州等地的方志的物产项中,皆不见有玉蜀黍的记载。农作物中,裁培不多者,是像少量的药草一样,在方志中是不一定会被采录的。
|
二、 |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一大部分专记植物。『本草纲目』开始附有图画而记载玉蜀黍,谓玉蜀黍是由西土传来。所谓西土,是被解为明代的西番,亦即是指青海地方。民间的传闻,不一定十分正确,故以应解作泛指自甘肃至云南的西藏高原的东麓。
迄今为止,一般以为玉蜀黍的传入中国,是距『本草纲目』刊行的年代不远**。但李时珍与田艺蘅,其着作的刊行,在其生前皆未完成。故玉蜀黍之见於中国,可推测其当远在该项书籍(于按:指留青日扎与本草纲目)的出版年代之前。
这一观点,自De Candolle起,至现代的万国鼎、天野元之助为止,都是相同的。其前提是在哥仑布到达美洲以前,旧大陆上根本不知有该一作物。
据万国鼎等,中国方志中记载玉蜀黍最早者是安徽省颖州志,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刊行**。这是与葡萄牙人始至广州同年。吾们不能想像在该一年开始栽培的作物,立即记载於方志的物产部中,故其传入在该一年代之前。万国鼎推测谓顈州的栽培玉蜀黍,可能是在哥仑布发见美洲後不到十年的时期中。
于野元之助与笔者皆尝调查日本内阁文库的顺治(1654)颖州志,在物产项皆未见有相当於玉蜀黍的作物,故未能确证万国鼎之所云。但清初的方志,其内容很多并不继承明代的方志。其显着的例证,是大清一统志的编辑,完全没有考虑大明一统志。再有,在水田植稻的地方,玉蜀黍是夏季的旱地作物,亦许古时虽尝栽培,而後来却已衰微。万国鼎教授等在刊行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时,尝调查全国的方志,故万氏之言,似可信任。
如果万氏的见解是正确的,则不能不考虑此项传布如何方才是可能的。如果这一说明甚为困难,则De Candolle 尽管否定,吾人却不能不推定在哥仑布以前的时代,亚洲已经有可能是有着玉蜀黍的一种。事实上,甚至在美国,亦有具有这一意见的学者**。
E. Anderson及其共同工作者,有此主张。
纵令玉蜀黍的发生地是在美大陆,而在哥仑布发见美洲以前,玉蜀黍的栽培已扩到美洲以外**,则不妨假定在哥仑布以前的某一时期,玉蜀黍已有一个品种传达於旧大陆的某一角隅。其间并没有什麽矛盾。例如丹麦的航海者、西伯利亚的某种族、或是Polynesia-Melanesia居民的活动,皆可能具有着媒介的性质。
据美国的研究者,在旧石器时代,尝发见有玉蜀黍的花粉。据此推定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己尝利用玉蜀黍。英国伦敦大学的学者,推测亚洲系的玉蜀黍是发源於缅甸北部附近,但似不决定以玉蜀黍的起源为在亚洲。关於这一点,是与Michigan大学的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者谈话後确定的。参阅古野清人:原始文化扎记pp. 49~54,(1967)。
本草纲目的图画,据说是李时珍之子所绘。这图决不能说很妙,故不能据以讨论细微的部分。但一方参阅记载,可知所绘者确玉蜀黍无疑。记载曰「苗叶皆似蜀黍」「肥矮亦似薏苡」,图中所绘者是叶间的节间很短,高是三、四尺,顶上抽出一花蕊,而并列着一有毛的穗**。穗上的子实是粗粒,而排列不整。柄长。其形态与蜀黍类似。这或许是为要将雌穗轴明白显示起见将苞叶及叶的一部分除去後所绘的图,看上去很奇怪的地方,都是波斯型玉蜀黍在形态上的特徵。
李时珍的记载,穗须是白色,故与田艺蘅所观察的品种不同。「以火炙之,爆为白花」,这是指示着是糯的品种。糯的玉蜀黍,作为突变,各地皆有出现。但纵观世界,作为糯的玉蜀黍的品种群,与其他谷类之糯的品种群,共同形成为地方的特色者,是限於云南缅甸地区。故李氏的记录,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大概是云南缅甸的糯玉蜀黍的品种群已传入李氏观察范围的长江流域,较为妥贴。(于按:云南缅甸区域的的谷类的糯的品种,确是一项特色。该一区域的居民,是以糯米为食粮。玉蜀黍的糯的特性,英文符号所谓waxy者,是在该一区域首先发见的。)
李时珍父子所观察的。可使人推测这似是沿着喜马拉亚山系分布的产於中国内陆深处的玉蜀黍(图一)。

图1:(左)植物名实图考所载1848 。(右上)初版本草纲目1590。(右下)承应和刻本草纲目 1653
这一植物给人的全体的印象与N.N.Kuleshov所揭示的波斯型玉蜀黍的相照(图二)甚为近似**。古今图书集成亦采用本草纲目的这一个图。故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似是异样的形态,似可考虑:在当时却真是表现着玉蜀黍的形状。
图2:(左)Bokhara所产波斯型玉米。(右)N.N. Kuleshov, 1929 将左图去叶後
但清朝後期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则与『本草纲目』中者不同,相当是写实的,有旗叶,节间短,叶长,叶绿皱,苞叶将子实完全遮掩,其形态是作爱琴海型。这是在亚洲各地很普遍地可以看到的形态**。至少,在农学者方面,可以看出这与『本草纲目』所示者是不同系统的品种的写生图。
H. H. K
故明代散在中国本土的玉蜀黍与清代中期以後扩大栽培的玉蜀黍品种,很明显地,其系统是不同的。至於近时的『五谷史话』,「玉米」中所示的图,则皆为日本及中国沿海岸很普通的Caribbean Type的玉蜀黍。
|
三、 |
天野元之助氏尝追踪玉蜀黍栽培地区的展开过程,欲求阐明玉蜀黍在中国境内的传布途径,其结果不一定可说是成功的**,在比较新近的历史时代引入中国的作物,在各地方志中,其内容纵或不一定十分正确,但皆带有说明,说是外来的。
天野元之助1962中国农业史研究。p. 53~58.
一般传说是由於张骞传入的西瓜葡萄,时代很古老,栽培很普遍,在方志中,大抵皆不载来源。但可视为与玉蜀黍同传入的美洲大陆原产的作物如马铃薯、甘薯、落花生、烟草等。则在各地方志的物产部中,大抵皆附记其来源。试举数例如下:
「淡芭菰」种出东洋。茎叶皆如秋菊而高大。邑人多植之,切为白丝,蜀中之名品也。称曰白烟。(四川遂宁县志,一七八七)。(于按:遂宁县志文是据日文译出,未及对照原文。)
「番薯」一名甘薯。根叶皆可食。其种有朱者,有白者,有皮肉俱红者。明万历中得之吕宋国。凡沙砾之地亦皆可种,不甚费人工。(福建漳浦县志卷二,1700)。(于按:漳浦县志文,尝覆按原文。是民国十七年翻印本,有康熙三九年序,原序年号作嘉靖。)「马铃薯」洋种传来,亦合土宜。(福建建瓯县志一九二八)。(于按:尝覆按原文。)「落花生」为南果第一。以其资於民用者最广。宋元间与棉花、蕃瓜、红薯之类同为粤估自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落花生曰地豆。……今已遍于海滨诸省(檀萃,滇海虞衡志)(于按:尝覆按原文。)
即在中国方志或其他记录中,对於新来的作物,大抵皆传述其由来。如玉蜀黍是由同样方式传入,则似应有同样的记录。但是,祗有玉蜀黍,在本草书中,是说来自西土或西番。这究应如何解释?如笼统地说是因民众没有传述正确的知识,似不能说是一谨严的解释。要之,至少就玉蜀黍这一农作物言,在中国方志中,绝对没有丝毫迹象说是由萄葡牙人自海道传入。笔者不明白玉蜀黍之传入中国,为什麽一定要与葡萄牙人之东来联结在一起?或一定要规定玉蜀黍是由哥仑布方引入旧大陆?如有明确的根据,布望读者仍提供。
如果没有根据,则在现在的常识上纵或是可笑的异说,似亦有加以检讨的必要**。玉蜀黍的乾燥种子,一个旅行者可携至很远的地方,故其栽培地很可能分散作点状。至若某处的居民完全食用玉蜀黍,玉蜀黍形成为定居农耕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大概是要相当长的期间。
例如Swingle谓中央细亚的回教徒在十六世纪中叶由麦加传入新疆或西藏,而由此传入中国本部(W.T. Swingle 1934 Maize in China. Nature, 133:420.)。关於这一见解,笔者是不同意的。
若作为珍奇植物之一而予以栽培,则其栽培是有限度的,纵或一时性地可成为特产,而要继续发展成为产业是须要着各色各样的条件。据此观点,则在方志类中,止於一州一县的小域时,在量方面,可说尚是不安定的。例如正德顈州志的记载,在後代的物产项中,是把玉蜀黍除去了的。如果不止於一府一县,例如在各省的通志中,其栽培涉及於广大区域者,则对於其开始记载的时期,应可视为在该一时期该一作物栽培已久、并已安定的证明。
中国的玉蜀黍这一正式的名称,是由『本草纲目』而方为学术界所知道的名字。在『本草纲目』之前,是称番麦,即以为麦的一种。或称包粟、珍珠粟,而视为粟的一部分。此外尚有苞米、棒子、玉榴等俗名。至如观音豆,鸡豆粟的称呼,则如无预备知识,实无法想像其所指者为玉蜀黍。但是根据该项名称,要确定其为玉蜀黍,有时是有困难的。例如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引直省志书,把当时普遍的名称玉麦、番麦,皆包括收录在麦的项下**。
中国以荞麦亦纳入麦类中。故中国之所谓麦,大概是泛指磨粉後食用的谷类。中国人以前对於玉蜀黍大概亦是磨粉後食用,故亦称曰麦。玉字大概是因其谷粒的光泽而来。云南大姚县志曰:「其用适与谷麦无异」。
至最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则毕竟是不同了,不再误以为麦。但『五谷史话』中所记中国各地方志中的有关玉蜀黍的名称,究竟以什麽根据决定其为玉蜀黍,则不无若干疑问。例如被视为中国第二部最古的方志,是1531年刊行的嘉靖广西通志(在日本内阁文库中不是有此本),其中有语曰「稷俗名明禾」。『五谷史话』以为指玉蜀黍。其根据何在,并无说明。
在万历太平府志中有语曰「稻,太平之人名曰畲禾」。这是土人以稻(大概是旱稻)与普通的烧田(畲)作物相区别的名称。广西通志谓「稷曰明禾」者,大概是因土人本来种的是其他的杂谷,而新来明人将稷携入,故称明禾。这稷,按传统的解释,是指後人所说的粟(Setaria),据後人转讹,是指高梁(Sorghum)。
其次,在台湾出版的明代方志选中,有万历广西通志。其中不见有相当於玉蜀黍这一作物的名称。『五谷史话』究属有何根据决定谓明嘉靖时在广西已有玉蜀黍,其说殊不可解。同一皇朝的皇帝的交替,而重修一个地方的方志时,对於前代的方志,完全不加参考,大概是不可能的。
要之,在『五谷史话』中,检讨各地方志的物产的结果,在明代有玉蜀黍者,是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在此处,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玉蜀黍如果是由南海路线传入,而在明代的浙江福建二省的方志中,却不见提及玉蜀黍之名。但田艺蘅是浙江人,李时珍是湖北人,田李二氏已在其乡里实在看到了玉蜀黍,故在明代末叶,不妨视为玉蜀黍已散布於中国的全境。如谓玉蜀黍之传入中国是在明末,并只有南海一条路线,则在短期间内,其散布会如是之广,是不很容易使人理解的。
在另一方面,如欲根据地理分布,以求知其传布的途径,则根据方志的省别的分布,不很容易进行研究。然如根据州县的记录,以推测栽培集中的程度,则或可据以推测玉蜀黍在某一区域的栽培时期的长短,即或可推测某一区域引入玉蜀黍的迟早。又如同一地方的方志,连续记载有玉蜀黍,则可推测其栽培量多,若在旧志中有而在新志中消失,则似可推测其栽培量减少,而已失去其重要性。据此原则,则在十六世纪中叶,已广泛地栽培玉蜀黍的,有云南省的大理、蒙化、永昌、鹤庆、姚安、景东等六府,即金沙、澜沧、怒江三大河自西藏高原流出而将要分开时高原区域,似为集中栽培着玉蜀黍的场所。
上述区域之各地区中的详细的分布,则要到後代方才明白。惟在该一区域的大部分的县志州志中,皆记有玉蜀黍,其说明亦极为详细,故似可推测玉蜀黍是很早已在该地普及的作物**。该一地区紧接於所谓西番之南,而是在西番与明代苦心讨伐的金齿、平缅、芒巿等蛮族诸卫之间,故在中国本土言,是很容易与所谓西番相混淆的。
云南许多县志,对於玉蜀黍的说明极详细。上述大姚县志,对於作为食物的使用方法与栽培法,皆说明极详。
西藏有谚语曰「有犁牛处不长玉蜀黍」**,真正的西番,例如青海,温量指数不足,玉蜀黍的发育困难,故作为玉蜀黍传入中国本部的传布基地,无基意义,是一如De Candolle之所指摘。
据中尾佐助教授的指示。
De Candolle是不承认玉蜀黍西番起源说的。事实上,在四川西部的藏族居住区,到清朝末期为止,玉蜀黍尚未传入**。
四川松潘纪略(1873)记有栽培经过。
但是,湄公河上游原在人民的秤戛野人的区域,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方并入清室的领土,其染齿成黑色,面上亦涂颜色,而其人是以包谷,即以玉蜀黍为常食。稻及其他作食粮用的植物,栽培极少**。故吾人当可承认其很早已将玉蜀黍包摄於其农耕文化中。纵令说哥仑布自美洲将玉蜀黍携归旧大陆,再传入广东,试问是谁再将这种子传入如此偏僻秘奥的地方?
汉军:滇南新语,收录於小方壼斋舆地丛书中。
上述栽培玉蜀黍的区域,不是西藏贸易所经由的道路,故由回教徒经由新疆而搬运的可能性极少。除开与缅甸北部的原住民作种子交换以外,该一区域的居民,大概没有其他方法可获得该一植物。因为在该一时期,以中国本土言,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尚有很多地方不见有玉蜀黍的栽培**。如上述推理是正确的,则该项野人栽培的玉蜀黍的品种,大概不会是由葡萄牙人东传的Caribbean Type。关於这一点,今後的野外调查,大概是会证明的。
参阅湖广通志、四川通志、福建通志。
|
四、 |
在云南西部高地分布甚密的玉蜀黍的栽培,究系始於何时,现尚不明。但栽培遍及於四万平方公里的山地全境,其传布决不是一短促的时期。葡萄牙人到达印度西岸是在16世纪初叶,而中国文献中有玉蜀黍出现,是在16世纪中期,这短短的50~60年会传布如是之广,实很难想像。因就当时的玉蜀黍言,与稻及当地已有的旱田食粮作物竞争,玉蜀黍实在不能说是一丰产的作物。
关於这一点,稍後另当有说。但云南栽培玉蜀黍,亦决不能说很古,故亦不能考虑其为玉蜀黍的原产地。例如樊绰的蛮书,关於云南的农耕,记述颇详,而没有提到玉蜀黍,续云南通志稿中记有原住民的方言,如稻、大麦、小麦、燕麦等主要谷类,是列记着夷族、泰族、白族、罗罗族等主要种族给予该项谷类的名称。但对於玉蜀黍是只举示罗罗族、白族的Zhou-mo而其他种族皆无相当於玉蜀黍的名称。这是指示着玉蜀黍的传布尚未普及於全部的原住民而似是一比较新的作物。
在记载明末清初的物产的直省志书中,玉麦之名是见於河北省清苑县、山东省历城县、河南省昌邑县、延津县。在现在,玉麦之名,在云南省,是限於西北部;在省城昆明,是称包谷(包谷),这是由贵州扩展到云南的名字(24)。其他如四川省西部,亦尚留有玉麦之名。据此以观,玉麦之名,在中国,尝广布於各地,而现在是残留於偏僻的地区。
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1964汉语方言词汇。
在清初,有玉麦的地方,现在是称棒子或包谷,这是指示着後代的新的名字压迫着旧名玉麦,而使之趋於消失。又如江南地区通称的番麦,现在袛是残留於福建厦门、同安,而江南却是用俞卖(于按:当是玉麦的写音)棒头等新的名字**,此项方言变动的原因之一,或可考虑是因新品种出现,代替了旧的品种,因此联带着使旧的名称消失。例如云南本来的旧品种的玉麦,因有称曰包谷的丰产的新品种自贵州进入昆明,与昆明之西的玉麦区域楚雄接触,其结果,在楚雄地区是产生了新的名称曰包麦。十九世纪末期云南地区有关玉蜀黍的方言的分布是如第三图所示。
汤起麟,玉米p.1,列示苞萝、六谷、玉茭等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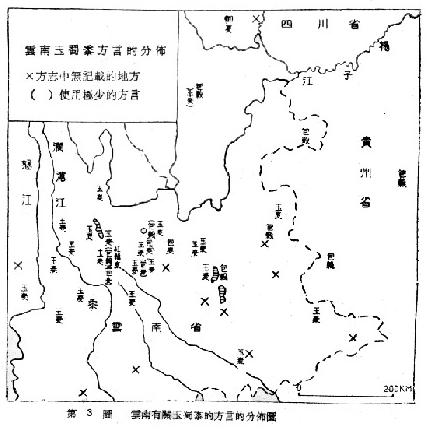
在道光二十五年(1843)的姚县志中,并举玉麦与包谷,而列述二者之异曰:「包谷即玉蜀黍,一名玉高梁。其状,茎如甘蔗,高七八尺,每节叶间出一苞」。「玉麦似甘蔗而矮,每株二三苞不等」。南宁县志引道光十五年(1835)的云南通志稿曰「大麦小麦燕麦三种植於陆地;玉麦植於园中,似芦而矮」。据是则所谓包谷与玉麦,似是在高度上有着差别,即包谷高而玉麦矮。就野外观察的观点言,似可推测这是Caribbean Type 与Persian Type之异,而大概在产量上亦有着差别**。
Caribbean Type玉蜀黍的典型,见於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这可视为葡萄牙人自Caribbean sea携来的系统。
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绩云南通志稿中,有很值得注意的记载。其言曰:「谨按,玉麦形似包谷,惟其苞大而子实小,不成行列。」据此以观,可说:称曰玉麦的玉蜀黍系统与子实排成行列的Caribbean系统。在系统上显然有别,又玉麦的粒色有蓝红等,且多糯的品种;而属於包谷的系统,其子实有黄紫玛瑙等色,而大多是硬质,或似齿粒种**。
汤起麟,玉米,p.2。
子实小而排列不整齐的玉麦,每株的苞数少,故其产量大约不高。至称曰包谷的新品种,是由东南进入,每一节叶间有苞,自高度以观,可推测其为Caribbean Type**,其产量高,故似很快就普及於各地。此项推测,将来的实地调查,将可证实。尽可能的文献的研究,当可在作实地调查前,先建立一项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
大姚县志曰:「每节间出一包,如冬笋。绿箨数重裹之。箨似竹而软,中有胎,如茭笋,根大而末锐,其格如之房子,格中居然有蛹土在,平铺密缀,如编珠然,初含浆,渐实渐老,或黄或白或紫或赤,五色相鲜,箨颠吐须,如丝如发,色紫而绦。每茎或四五苞,或二三苞。茎顶有穗。正似薏苡。」据是以观,可知称曰包谷的系统,决不是如『本草纲目』所示玉蜀黍之于实裸出的系统,并与玉麦似的子实不成行列者亦不同。(于按:本节中所引方志文,皆系自日文译出,不获与原文对照。)
|
五、 |
上云,要根据文献先作准备的研究,但在日本可利用的文献,与中国本土比较,在数量上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问题,作有效的整理,俾使用在日本可获得的资料,亦可作某一程度的研究。这样的问题,可举示者有三:
一般相信的由葡萄牙船携来的新大陆原产的农作物,其由葡萄牙船携带的确实性如何?
调查在日本可获得的中国方志及文学书等,检讨明代文献中所载的玉蜀黍的名称形态,并追溯记载的年代。
主要的是根据方志以追溯新大陆原产的农作物在中国境内的传布途径及其年代。
研究的目的是玉蜀黍,但玉蜀黍是新大陆原产的许多农作物之一,此外尚有烟草、甘薯、落花生、马铃薯等,亦皆为美洲原产的农作物,这大约是在同一时代自海外传至亚洲,传入中国,故对於玉蜀黍,似不应视单独传布的植物。在亚洲,玉蜀黍是由於外来文化刺激所一形成的复合食物文化的要素之一,这似应与同类型的作物群包括在一起,而一同考虑其传布。质言之,吾人对於玉蜀黍的传入中国,是应视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或应视为文化复合之地域的形成的一项地理学的问题,而加以处理**。
薮内芳彦、饭沼二郎译,Emil Velt着:农业文化的起源(1967)。
关於上列三项研究题目,就第三项言,笔者的研究,尚不及一半,其报告当俟诸异日。现将就第一及第二项,叙述笔者考察所得,以就正於方家。
关於第一项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日本的研究者,在常识上,美洲原产的作物,由南蛮传入的印象,皆很深刻。故对於种子、岛铳(于按:即步枪或手枪)、烟草、基督教、纱布等复合文化的内容,皆有一种先入之见,以为当然是由葡萄牙船传入日本。关於这一点,实在有对於史料作详细检讨的必要。就中国言,大概亦是同样的情形。关於中国人(汉民族)本身的意识,外国人很难作深入的探讨。就文化复合问题言,往往有以一推十的倾向,这一点,在研究者似是不可不戒慎的。
试举实例。甘薯、烟草是经由九州平户传入日本**,在日本首先栽培甘薯者是英国的领事馆员,但日本人遗忘,而往往以为是与洋枪一同由葡萄牙人传入。但这是因日本与海外诸国的接触大多是平稳的情形下进行的结果。日本人往往以为中国人与外国的接触亦是同样的情形。笔者在此处要特别指出,事实上不是如是。
参阅村上直次郎编:异国丛书(村上直次郎,贸易史上的平户;宫本常一,甘薯的历史)。
矢野仁一对於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关系,有极详细的研究**,据是则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交涉,绝非平稳(于按:至今遗留的创痕,是澳门),在此期间,很平凡的农作物如玉蜀黍与落花生,是不是会传布,实为疑问。就与中国的接触是不是平稳言,葡萄牙人与後代的大西洋人(意大利人)是不同的。现在根据矢野仁一的考证,先略述葡萄牙人与中国接触的经过的大要。
矢野仁一 1928中国近代外国关系研究。
葡萄牙王於1508年令人探视麻六甲,其使节为麻六甲王所抑留,葡萄牙遂於1511年攻占麻六甲。1514年,即明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始出现於中国,进行着商品交易。交易的场所不明,矢野推测以为商品是积载在南洋船或中国船上,而葡萄牙人只是以乘船人员的一部分的身份东来。
农作物,并且是极平凡的食用品,大概不会被携带作为交易用的商品。南洋船或中国船上的船客的葡萄牙人,如只是积载着交易用的货物,则大概不可能以其食用作物传布於交易对手的国家的农民。据葡萄牙人的文献**,中国是禁止其人民出至海外,故居住於麻六甲与南洋各地的汉人(即华侨)各皆自称为居民住地的王的使臣,而往来於中国及其居住地之间。
Gaspar Da Cruz:Tractado da China,据藤田丰八转引。
实际上,这样的外国籍的汉人,大约为数不少**。如葡萄牙人所雇用的,是这样的中国船,其食粮流入於中国农民之手,而被用作种子的机会,大概极为稀少。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四。据矢野氏转引。
葡萄牙船直接到达中国,大家熟知者是正德十二年(1517)。据筹海图编,佛郎机人(于按:其时称葡萄牙人日佛郎机人,称荷兰人曰红毛人)是到达广东怀远驿。又据万历三十年(1597)的广东通志,「佛郎机本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驶大舶直入广州湾,以进贡物为名,发射大炮。中国官吏,以如此进贡,无前例,止其行。彼等止於东莞县之南头,设住居,围栅警戒而生活」(于按:广东通志文,是据日文译出,未覆按原文)。明实录,明史的记载大体相类。
此时,吾人在考虑农作物的传布上,要注意的,是:佛郎机即葡萄牙人是假借着进贡的名义。在他们,是随着欧洲人的习惯,大概以为如是则在通商的交涉上比较有利。但明庭的习惯,则对於正式的国家使节,是禁止着其作私船的贸易。故葡萄牙人纵令在船上装载其本国或南洋的产物,一方进行其官式的交涉,一方经营走私的贸易,在其要保持官方使节的名义下,其走私贸易,应当是受着很大的限制。
如矢野氏之推测,佛郎机人在被抑留的数年间,可能是以其一部分商品进行着走私贸易,但当然是秘密行为,故其商品内容,当系限於少量而高价的货物,如落花生或玉蜀黍之类,其买卖或交换的可能性,大概是极少的。
并且,再有一点须要注意:即该项新大陆原产的食粮用农作物,在其时的葡萄牙,大概产量亦不会多,纵令在航海时,有一部分玉蜀黍被用作食粮,大概亦只会装载於葡萄牙人自己的船只,而不知道该项农作物的南洋船或中国船,大概是不会加以利用的。故从作为货物的价值看,从与中国农民的接触机会看,葡萄牙人直接将玉蜀黍传布於中国本土的可能性,决不会多。
从上述观点看,嗜好品的烟草,其情形或稍有不同。烟草是有着被利用为交易物品而很迅速地传布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广东省内烟草栽培之发达是在清代中期以後,并且,由福建湖北方面传入之说,甚为有力**,这就是说,像烟草似的强有力的农作物,航行至广州的葡萄牙船,在传布上,亦未见有显着的作用。
光绪广州府志谓「烟草来自南雄湖北方面,为广东本来所无」。道光南雄州志谓(1753)「旧志未载」,故以为广东栽培烟草是不久之事。江西省方面,广信府志瑞金县志谓烟草来自福建。(于按:上列方志,皆未及检视原文)。
此处要注意的,是葡萄牙之向广州的正使Tome Pyres一队的影响,实在说,是不如其向福建漳州的福使George Mascarenia的船队者之大。这是因Pyres一队在广州被抑留二年,以後虽获到达北京,而其後到达的Simon de Andrade发挥了各大种暴行,故受着中国人的排斥,嘉靖二年(1522),在广东省,经过战斗,葡萄牙人完全被赶出广东。换言之,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广东的初期的接触,决不是和平的,而很显着地是敌对着的。故纵或有农产物的交易,其效果决不会大至可对於後世发生影响。
惟在漳州的葡萄牙船与中国居民的接触,却不像在广州似地是战斗性的,而比较和平。福建省同安县人林希元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与翁见遇别驾书」曰: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他之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沈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最平。其日用饮食,皆资於吾民。米面猪鸡之类,价倍於常,故边民皆乐与为巿。迄未侵我边疆,杀戮人民,劫略财物**。(于按:爻布元信是由日文译出,未获覆按原文)。
藤田丰八1918 葡萄牙人到占据澳门为止的许多问题,东洋学报8(1).
这似可视为和平通商。後代的漳州,作为中国的烟草产地,尝为一方之雄(36)。
晋江县志(1765)谓「土烟不如漳」,龙溪县志曰(1762):「惟漳烟称最」。
又林希元家乡同安县的邻县安溪县的县志,在福建省现存的方志中,是比较上很早记载着玉蜀黍的方志**。故葡萄牙航向中国传入农作物的可能性,或可考虑漳州的路线。葡萄牙人在被广东逐出以後,时间及理由,皆不甚明了,是在浙江宁波府出现,在称曰双屿的岛上经营贸易。
安溪县志(1757)曰:御米一名番麦,穗生节间。
藤田丰八**推测曰:葡萄牙人大概是因日本人在宁波与明人贸易甚盛,故可能是以双屿为转接地点,而进行着与日本的贸易。但葡萄牙人在双屿的和平贸易,亦不能长久维持,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仍被驱逐。此处,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与宁波府接近的杭州府,在万历七年(1583),已有落花生存在。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当时的大部分的中国官吏,对於葡萄牙人皆甚厌恶,甚至有人说:与其他国家的船可以交易,而对於葡萄牙船,则无论如何,一定要加以排斥**。
据藤田所引文敏公全集卷十下「两广事宜」文。
其理由,有若干事件可以考虑,而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是:Simon de Andrade的暴行。传说:葡萄牙收买中国婴孩而加以杀害,故对於佛郎机抱有好感的爻希元亦曰:
佛郎机虽无盗贼劫掠之行,而收买子女,不能谓为无罪。推其罪尚不至於强盗。最可恶者,为掠取边民,以行买卖。总之,葡萄牙人贱视亚洲人民,以之为奴隶而肆行买卖,大概是被当时的中国人厌恶的最大的原因。
葡萄牙人的交易方式,据在广东省负警备责任而强硬主张排斥佛郎机的朱纨的「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是如下所述。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佛郎机人)驾船在海,以胡椒银子换米布紬缎,以为买卖,往来於日本漳州宁之间。……在双屿,有不知名客人,操小南船,载面一石,送入番船。谓有绵布、绵紬、湖丝,编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幸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银百两谓买缎子、绵布、绵紬……
这是说,佛郎机人以银购入中国工艺品,或是运入南洋的物产,以卖於中国居民,而购入当地所产的粮食。在这样的交易方式下,似很难期待葡萄牙船会运来农产种子,以推广於中国居民之间。并且葡萄牙人的贸易,大多是船在海上,进行着商品的授受,故似可曰:葡萄牙人并没有在陆上定居,以试行植物的栽培。
1554年以降,佛郎机贸易,获得中国官方的准许,葡萄牙人居住於澳门,以後的通商关系,比较平稳,但葡萄人的居住,自成群落,皆密集於巿街,而极少园地或耕地。这一点,从最初在广州被拘留时代起,一直到後代为止,似无变化。据庞尚鹏疏,是说:(佛郎机人)近顷数年来,始入蚝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几已达千区以上。
其密集居住的形状,可以想见。俞大犹书亦记其未获准许而强行居住的状态曰:商夷以强梗之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
万历广东通志记其占居状态曰**:
托言舟触风涛,愿借蚝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茅舍。商人牟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为所据。蕃人之入据澳,自汪柏始。至万历二年建闸於莲花茎,设官守之,而蕃夷之来日益众。(于按:本文是据澳门纪略上卷修正)。
T. Suto and Y. Yoshida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maize,in H. Kihara (ed.), Land and Crops of Nepal Himalaya. p. 373~519. Kyoto. 及所引文献。
据此可知葡萄牙人占居中国的土地,是过着与当地居民隔离的生活。故葡萄牙人在澳门虽是过着陆上生活,其传布农产物的机会,亦显然受着限制。事实上,在澳门所在地的香山县及其附近地区的方志中,到清朝末期为止,未见有新大陆原产作物的记载**。
道光香山县志(1827)举有和兰豆、粟米(是指玉蜀黍)、甘薯、落花生,关於和兰豆,记曰:近数十年来自澳门获得种子。其他皆未详记由来。只是说:甘薯得自诸番,和兰薯来自外国。所谓和兰薯很可能是指今谓马铃薯。和兰豆(菜豆),在福建漳州方面,乾隆初年(1740年代)己载於方志,故经由澳门的传布,是远在其後。
|
六、 |
如上所述,根据方志的记载,玉蜀黍之广大的栽培区域,是以云南省西部的大理府为中心而展开。这是明万历初年(1576)的事情。如以该项栽培的种子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初获准居留於澳门的葡萄牙人所传布,则以广东与云南相隔之远,加以当时交通之不便,在时间上实太嫌局促,而不能无疑。
在比较更早的时期,有没有文献指示出云南是栽培着玉蜀黍?云南方志的编辑,是以明万历年间者为最早。故据云南的方志,很难再向前溯。但在本草书及游记中,或可求取更早的记录。至此,最先受到注目的,是『徐霞客游记』,徐氏在万历天启崇祯间游览中国中南部的山地名胜,而遗有详细的观察记录**。徐氏足迹遍及广西云南,且远至缅甸境界。故对於其记载,殊有详加检讨的必要。笔者尝详检香港广智局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版本的『徐霞客游记』,皆不见有有关玉麦或类似名称的作物的记载。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于:版本从略)
所谓游记或文学书类,往往有当地人视为日常普通的事象,不成为记录对象,而在外来游客,却视为新鲜而予以记录的。故游记类有时可成为极有用的资料。但徐氏在云南的大部分的旅行,是在冬季。这大概是这一位很精密的观察者对於该一地域的特殊的农作物所以未有认识的原因,因此,依仗游记类的收获,碰运气的机会很大,在目前,希望不多。
其次是本草书。本草书当然是记载当地的植物、动物与矿物,就一般而言,是记载植物的数目较多。中国的本草书,其记载的植物,是以华北、华南平野丘陵者为多**。至住在云南而且直接观察记载云南当地植物的本草家,实在甚为稀少。
本草书中首先记载玉蜀黍者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但近於是同一时代或比较稍早的本草书,在日本有陈嘉谟着的『图像本草蒙筌』(嘉靖乙丑,1565)及李中立着的『本草原始』(出版年月不明)。二者皆藏於日本内阁文库。在前者记有御米。据其记载内容,是指Amaranthus(苋菜属)的一种。这是今後应当注意的植物。(于按:关於这一植物,千叶氏在另一文中有说明)。
但甚为幸运,在云南图书馆汇集的云南丛书子部中,收录有兰茂的『滇南本草』。兰茂是明初洪武三十年(1396)生於云南省云南府嵩明州,是当时的学者诗人,其学问上的活动,是在正统年间(1425~49),成化十二年(1476)殁,八十岁**。
于乃义、于兰馥 1957滇南本草的考证与初步评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第1号。二氏谓据需南方志十种的引证,则兰茂是承受着未周濂溪的学派,通医学、阴阳道、地理、画论,长於诗文,着述颇多,有韵略易通、声律发蒙、性天风月通玄记、滇南本草、医门要、玄壼集等。又务本堂本卷一往往有先生云云之语,故似夹杂着兰茂弟子之文。兰茂去世後,该地常遭兵燹,旧着多散佚。故兰茂亲笔的着作无遗留者,其居屋不复存留,亦无子孙(据嵩明州志)。
在『滇南本草』中卷,有「玉麦须」的记载,谓「焙乾可治女人乳肿」**。据笔者所知,这是有关中国玉蜀黍的最古的记载,而该项记载的时期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1492)以前。故该项记载如果是确实的,则玉蜀黍之传播於中国是始於葡萄牙船之东航或非在哥伦布发见美洲以後不可之说,自将云消雾散。
原文如下(云南丛书本):玉麦须味甜,性微温。入阳明胃经宽肠下气。治妇人乳结红肿,或小儿吹着,或睡卧压着,乳汁不通,疼痛怕冷,发热头疼,体困 。新鲜焙干,不拘多少,引点酒服。(于按:参阅图四)
但中国古代的文献,往往有後代的增补或掺杂,故为要证明『滇南本草』的真实性,一定先要经由严格的书志学的考证,证明『滇南本草』确实是兰茂的着作,而有关玉麦须的记载,确实是出於兰茂之笔,而不是由於後人的追加。这一工作,需要很高深的专门知识,非浅学的笔者所能胜任,但在目前,则只能尽笔者所能,试为考查,尚待识者的指正。
『滇南本草』,至少是有两个系统,而各有新旧的版本。关於这一点,试先看云南丛书所收版本的解题者赵藩的见解。赵藩曰:
曩闻之先君曰:相传辑云南药品者有三家:一沐国公琮,曰苴兰本草;一兰茂,一杨慎,皆曰滇南本草。沐杨惟传钞本。兰有旧坊刻本,其中有刘乾添注数条。刘不详何时何地人,死非兰氏手定矣。至新坊刻兰本,则太揉杂,且书中时称止庵先生,决为无识者窜乱止庵之书矣。惟道光中皖人孙兆蕙以同知官滇,其人习医工绘,得杨慎传钞本,兰茂旧坊刻本,乃合校而汇编之,凡得药四百一十种,分载兰杨之说,亦间附已说,自绘为图而刊之,曰一隅本草。其书尚可备医家之用云。剑川赵藩撰。
上文是民国三年(1913)版(于按即云南丛书版)刊行时的解说(序言)。关於这解说,在1957年,云南图书馆参考部组长于乃义氏提出若干订正的意见**。据是则沐琮不是在医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的人,杨慎只是陈述云南的动植物,作为本草书的记载,殊不足观。
于乃义、于兰馥 1957滇南本草的考证与初步评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第1号。
又孙兆蕙不是安徽人而是江苏人,至所谓「一隅本草」则遍查云南和地,不见此书。要之,于氏指出赵藩的解题文错误颇多。但于氏极反对「滇南本草非兰茂作而为後人假托兰先生之名所作」之说,又对於玉麦须野烟的记载为後代附加说,亦加以反驳。下文将引用于氏之说,以考察『滇南本草』究属是怎样的一本书。
在光绪昆明县志中,谓「滇南本草,旧传兰茂作而序文作崇祯甲戍(1634),故非正统年间兰氏之作」。道光云南通志,亦记有同样的意见。云南药物改进所编的『滇南本草图谱』(1943),亦以为『滇南本草』记有应为哥伦布携归的玉麦与野烟**,故应是哥伦布发见美洲以後的着作。以上所列,都是对於兰茂滇南本草成立的年代表示疑问的。
『滇南本草图谱』一书,笔者未获亲见。大概该书未尝传入日本。试据云南丛书本滇南本草,揭示其原文(于按:参阅图五)务本堂本者後文举示。二于氏以为此文所指者不是现在所说的烟草(Nicotiana tabacum)。现在所说的烟草是栽培种。所谓野烟,是指与烟草不同的植物。并谓在现在的云南地方,应尚有相当於该一药草的植物。据笔者所知,在烟草传入中国以前,福建已有称曰烟草的植物,例如康熙平和县志(1719)曰:「烟草长仅及寸,细如丝,可收油灯之烟。今人以小盘植之,置案头。一名虎须菖蒲。」大概是像石菖似的植物。野烟,或是指与此形似的野生植物。
但清时『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璿,对於该项疑问,有一很明白的答覆。『植物名实图考』记有相当多的云南的植物,吴氏因此校对过『滇南本草』的相当多的不同的版本,而发见有记有「正统元年」的识语的版本。吴氏以之与云南通志稿所引用的滇南本草对照,见文章及内容大不相同,故谓云南通志稿所引用者大概是经後人增补,而有正统元年识语者则是兰茂的原本**。
于乃义、于兰馥:前引文。
笔者在上文谓『滇南本草』可区别为两个系统,是据此而说。云南通志稿引用,而吴其璿指出有後人增补者,就是赵藩解题中所云坊间的新刻本。这新刻本是光绪十三年(1887)昆明务本堂所刻印。卷一分上下。卷一上有图。卷一下及卷二卷三皆无图。无图部分的内容,大体上与坊间的旧刻本相同,而记载顺序稍有变更。共记药品458种,其中有13种为重出。务本堂本的名称是滇南本草,兰茂的序无年号。又附刻有兰茂着的医门要上下卷。下文暂称这版本曰务本堂本**。
笔者是参照着大阪武田株式会社杏雨书屋藏本。
吴其璿所云有正统元年识语的版本,吾人推定其大体上是兰茂的原着,因为这是赵藩解题所云旧坊刻本。计有三卷。这被视为版本之一,而收录於民国三年(1914)云南图书馆编的云南丛书的子部。但这一版本无吴氏所见版本的正统元年的识语,只有本文,无图。又葛根、商陆、紫苏……等36种,无本文,而只注有处方。药品总数为280种,大半是草。对於这一系统的滇南本草,在这篇文字中是略称曰丛书本**。
爱知大学图书馆藏本。
务本堂本与丛书本的颢着的差异,是:第一,务本堂本卷一上有图,而此一上中所记的植物,几皆不见於丛书本。务本堂本卷一上最後有落花参,据图及记载,很明颢地可看出是落花生:故可指出这一部分是落花生进入云南以後所写成。
其次,务本堂本卷一上对於植物的记载法,与卷二、卷三者不同,其先记载者是各种植物的产状与形态。在中世纪时代,只是列举药品的味性药效,是本草学方式的记载,而务本堂本卷一上者是植物学方式的记载,这在记载方式上是一项很重大的转变。故对於务本堂本卷一上可以看出是接受欧洲科学影响後所写成。
丛书本则明显地是保持着古时的方式,是顺次记载着味、性、药效、主治,而完全不提到植物的产状与形态。大概是因务本堂本的记载方式较为新熲顈,故近代编辑的『云南通志稿』、『植物名实图考』大多是引用务本堂本,尤其是大多引用卷一上的部分,这可说是当然的**。
云南通志稿自滇南本草引用68种,其中有63种是自务本堂本卷一上引用。植物名实图考自滇南本草引用53种,而文字已经增减,故那一部分是引用的,并不清晰。
在于乃义的考证中,因科学性及有益性亦以务本堂本为『滇南本草』的主流,就其所取立场言,亦可说是当然的。然自历史的观点以视滇南本草的两个系统,则似可推测:丛书本是继承着兰茂原着的形态;迨经後人增补,至清初乃取新的记载方式,并重行编辑,其结果乃成为务本堂本。这务本堂本或许就是相当於赵藩所记的一隅本草。
七、
兰茂,据传是生於明初,而承受宋学系统的闽派的教育,故其所着本草书,当继承着中古时代的本草书的系统。云南丛本的滇南本草与务本堂者亘及全书的明了的差别,是:前者在药品名後,先记其味,次记其性;而後者是先举其性,後述其味。即记载内容的顺序不同。试以之与古本草书的体栽对照,则云南丛书本的滇南本草的形式,与本草经、名医别录者相同;而务本堂本与古本草书完全不同。
笔者以为兰茂是忠於传统的人,故不能承认务本堂本是兰茂的原着。
云南丛书本滇南本草与务本堂本滇南本草之有关野烟的记载,是如下所示:
云南丛书本(参阅图五)
务本堂本
野烟一名烟草(目录中作一名小菸草)
性温味辛麻,有大毒,治热毒、疔疮、瘫疽、搭背无名肿毒、一切热毒疮,或吃牛马驴骡死肉,中此恶毒,惟用此可救。
补注:吃此药後令人烦乱不省人事,发迷一二时後出汗方省,不必着惊。盖此药性之恶热也。
附案:一人生搭背,日久不溃将死,名医诊视皆言死症俱不下药。後一人授此草,疮溃调治全癒,後人因名:气死名医草。以单剂为末,酒合为丸者名:青龙丸。
试比较二文,可知本文是只有味、性、主治,而其余很明显地皆为後代的补记或附注。此项补记或附注,大概是後人传写利用时,据本身的经验而添入,以後乃遂混入於本文中。
野烟下注曰一名菸草,是後代误以为Nicotiana烟草的原因。其原形似当为「小草」或「小菸草」。因在药效部分记有对於动物蛋白的腐败中毒是有效的。而Nicotiana烟草对此病症应当是无甚效果的。据云南医师苏采臣之说**:在云南地方实际上是有称曰野烟的药草,具有着滇南本草所记的药效。这与Nicotiana烟草是不同的。
务本堂本滇南本草,在白花地丁项有注曰:性味前人无注治痔疮生管。云南丛书本,无右线部分。据是可知缺这一部分的云南丛书本是出於务本堂本所云「前人」之笔。同时,务本堂本云性味,故务本堂本的校订者就按此顺序而修改。务本堂本所刻兰茂的序文无年号,故是不是兰茂原文,殊为可疑。序中有「余酷好本草,考其性味」之语,以後的校订者,很可能是据此而先记性,後记味,但这是根据字面的解释。一般的本草书,其记录方式,都是先以口嚐其味,而後知其药性。在兰茂的序文中亦曰:「神农氏尝百草而知药性」。普通写「味性」时,很可能误以味为动词,故写作「性味」,但以前的本草书,其记载并不依照性味的顺序。
在注的文字中,可注意的,是务本堂本改云南丛书本的食为吃,改发晕走动为烦乱,改发背为搭背,改出头为溃。就注及附案的文体以言,务本堂本似是比较接近於清代的近似口语的文体。改食为吃或吃,是其显着的例证。务本堂本,这倾向,甚为显着。例如云南丛书本作三日五日,务本堂本改为三天五天,又改煎食效为煨吃好等,都是例证**。
出於中国语学教授铃木择郎的指示。
要之,注、案、方等皆为後人所附加,而可视为硕学兰茂的原着的部分,是只限於记载味、性、主治的本文。故云南丛书本在形态上是保持着古代的表现方式,而务本堂本,则根据形式,可推测是在明末清初时改写。
例如云南丛书本滇南本草的土茯苓项曰:(参阅图六)
这似是菌的一种。其本文是到五淋赤白浊为止,大概是治泌尿器病的。其下文说妇人红崩白带,附注有药的处方,这可视为由後人附加。文中又说到杨梅疮,这就是梅毒,这当然是哥伦发见美洲以後的疾病**。故对於该项记载可视为以後混入於本文。务本堂本将上项内容,分项列写,这颇有助於笔者的推测。
据E. H. Ackerknecht, M. D.? 1965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 及H. Zinsser 1934 Rats, Lice and History。梅毒,并无确实的根据可说是由哥伦布航海至美洲後携归;但在1500年以前,亦无明白的根据说可说旧大陆方面确有类似这一症状的疾病。故东方之有这一疾病,故东方之有这一疾病,应当说是在葡萄牙船出现以後。
务本堂本土茯苓项曰:
土茯苓 一名次饭团
子名遗仙粮
性平,味苦微涩,治五淋、白浊,兼治杨梅、疮毒。附方治妇人红崩白带。
土茯苓水煨引用红沙糖,治红崩。白沙糖治白带。又方治杨梅、疮毒。
土茯苓或一两或五钱,水酒浓煎服。
又方治大毒疮、红肿未成即滥。
土茯苓为细末好醋调数。
补注:子名仙遗粮,治杨梅、结毒、丹流等。
「妇人红崩」下有处方,杨梅结毒是兼治,皆不能视为原有的记载,据是则对於云南丛书本的土茯苓项可视为将本文及附加部分一贯地列记着,因此遂引致混乱。
据是判断,则吾人所重视的对象,即玉麦须项的记载,似极少後人附加的迹象。云南丛书本的记载是:
玉麦须 味甜,性微温,入阳明胃经宽肠下气。治妇人乳红肿,或小儿吹着,或腄卧压着,乳汁不通,疼痛怕发热,头疼体困。
新鲜焙干,不拘多少,引点酒服。
务本堂本是将性味颠倒,又误入为人,乳汁不通下作体红肿,怕冷作冷,头疼作头痛。此外无甚差异。在处方处,焙干作焙乾,作点水酒服。此中,处方是後人附加,可除去。如是则在内容上丛书本与务本堂本大体相同,都是记载着作为药品的玉蜀黍的花柱,毫不足异。自玉蜀黍的花柱中可分离出Flavone的配糖体(glycoside)的Isoqueucitrin,在现在亦利用以为利尿剂**。
据迤田桂太编,增补改订资源植物辞典(一九五七)玉蜀黍项。
这是说,其作用可促进内分泌机能。在当时,大概以为在促进乳腺的分泌上亦有效果。
丛书本滇南本草,包括野烟在内,共记载280种药品,现在已知野烟不是Nicotiana烟草,杨梅疮云云是後人补注,而玉麦须一项,在云南丛书本与务本堂本中,其记载的形式与内容皆无异处,故至少在笔者,认为毫无根据可视为出於後人的附加。
为郑重起见,试再检讨务本堂本卷一上的落花参的记载,有关卷一上的记载,最先要注意的是与卷二卷三者不同,是只记味而不述其性。根据这一点,即可判断务本堂本滇南本草卷一上是与一般的本草书以及同书的卷二卷三不同,是一种後代的方式。务本堂本卷一上的落花参项曰:
落花参 味甘热无毒,盐水煮食,治肺痨。生用水泻炒,用燥火行血,治一切腹内冷。
积肚疼服之即效。枝叶治铁打损伤敷处。小儿不宜多食,生食变为疳积,忌之。
所谓即效、跌打等语法,都是新的语调,似非出於兰茂的原着。此种表现,在务本堂本卷一上中是一通同的方式。在卷一上中随处可见有神效、其效如神等。但在云南丛书本与和云南丛书本接折的务本堂本卷二卷三中,完全不见有此种语法,要之,务本堂本滇南本草卷一上,其内容有落花生、杨梅疮的记载,而全部记载的方式具有一贯性,其物品皆为中国人所初见,故可以判断这是哥伦布以後的人航行至东方以後,由兰茂以後的所附加。
至如云南丛书本的滇南本草,则除开後人的附注及处方外,其药品的排列顺序,与务本堂本者亦颇有出入,吾人纵或可疑其非完全为原形,但关於药品本身,当可考虑其是保持着兰茂所的原形。吴其濬大概亦尝考虑这一问题,『植物名实图考』所引用的『滇南本草』的文字,是与後出的云南丛书本者相同,先记其味,次记其性**。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中华书局1963年版。
要之,在目前,经书志学(版本学)的检讨,『滇南本草』应被视为深通明代初期的语言学医学及其他学问的兰茂的原作,在後代尝有人加以补注。惟补注的部分,根据用字文体,大体皆可加以检定区别。至有关药品的味、性、主治症状的本文,则视为出於兰茂本人的记载,当不至有误。故其记载项目之一的玉麦须,如无明白的证据可证明其为由他人补入,则吾们应当承认在兰茂的时代,即15世纪中叶,在云南的一部分地方,确已有玉麦存在。换言之,对於滇南本草中的玉麦须,应当视以为有关玉蜀黍的一个系统的记载。
如视此一项後代所附加,则一般以为比较容易传布的新大陆的其他作物,例如烟草落花生等,应当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而皆不见於兰茂的着作中,这是一很大的疑问。关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似亦可作同样的考虑。如玉蜀黍是由葡萄牙人所传入,则理应尚有大约是同时期传入的其他的作物;而本草纲目所记载者却只有番麦。
李时珍广罗全中国的药物,加以记载,何以会不见烟草与落花生,实在很难说明。唯一的说明,是:玉蜀黍是经由称曰西番的地区传入中国,其传入中国的时期,是较其他的美洲起源的作物为早。所谓西番,就中国本部而言,似亦包含着云南与西藏缅甸接界的部分。在该一地区,如上所述,在明初,可视为已经是栽培着称曰玉麦的玉蜀黍的一个系统。万历云南通志、万历大理府志的记载,是指示着玉麦的栽培范围甚广,这应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
明末,云南省有很多关於玉麦的记载。清初的云南府志(1696),在玉麦外亦有西番麦之名,二者大概是有着形态上的差别,据此可知西番麦之名,大概亦很早已经通行。在此附带要说的,是笔者对於玉蜀黍由中国的所谓西番地区传布至东南地区的推测。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尝发兵征麓川蛮族酋长思任,这一战争延续颇久,至正统十四年(1449)方止。这一远征军的主将王骥,据说尝以兰茂为顾问,而听取其计谋。麓川地区,具体地是相当於现在的那一部分,笔者不甚明了。至於远征军,则是在中国东南部组织,明史王骥传谓徵集江苏浙江安徽人员15万人而编成。後代的扬子江下游地区的记录中,屡见有番麦,西番麦之名,据笔者的推测,很可能是由该项远征军残存者携归的种子所繁殖。据行军记录,可推测该一军队尝到达缅甸的中部,甚或尝到达其北部。当时,该一地区尝栽培亚洲型(于按,即所谓Persian type)的玉蜀黍,大概是很确实的。但笔者不是说该一地区是玉蜀黍的原产地,只是以为可能是在哥伦布以前的某一时代,由某一路线,有玉蜀黍的一个系统传入该一地区。其详细情形,则尚有待於今後的研究。
原载:http://seed.agron.ntu.edu.tw/cropsci/maize/yu01.htm
《春雨逸响》 (明)田艺蘅 撰
春雨逸响 (明)田艺蘅 撰 ◎序 春雨闭门,良朋偶至,雅谈终日,无非金玉之音。退而纪之,用志毋忘逸响云尔。钱塘田艺蘅子艺。 尧舜之爱身甚于爱天下,故让天下干许由、务光而不吝。许由、务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尧舜之爱天下,不如爱子,故不以天下与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让天下与舜禹而不争不贤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苍梧、会稽之祸。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国而死于四夷。 形如稿木,不死之真心,如谷种长生之仁,死生不测,造化之神。 隼虽鸷不能攫凤,虎虽猛不能搏麟,人患不麟、凤,若尔于隼、虎何患哉? 周公吐握以来天下之士,今则州县之官尸于位,士有自至于门墙而不得一见者矣。或有见刺而诡却云:“饮食沐浴者矣。”谁能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也哉?夫以守令尚如此,又况于元圣之德,叔父之亲,冢宰之尊者乎?吁!世道人情两可识矣。 耕,男之职也。今之业耕者,毁其锄犁而教其子以盗;织,妇之事也。今之业织者,毁其机杼而教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织也,得饱暖;而今之耕织也,饥寒因之矣。耕织反不若淫盗。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袜系解,自结之而弗役其所与处,君道也;武王伐纣,而袜系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结,臣道也。周之君臣两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将自结耶?臣将结之耶?一举足而见之矣。噫! 进速必退,成速必败。《易》曰:“咸速也,贞者所以善其速者也。”言久必错,步久必弱。《易》曰:“恒久也,贞者所以善其久者也。” 正月之令,以东风解冻为始;十二月之令,以水泽腹坚为终。天地之启闭皆系于水,故曰:“天包地,水包天,极浮水中,水周极外。” 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人之初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 地以海为肾,故水咸;人以肾为海,故溺咸。 天道体明而用幽,故其福善而祸淫也,章章而昧昧;人道体幽而用明,故其赏善而罚恶也,默默而察察。 短狐射光而病疡,蛷螋溺影而成疾,此有情而无情也;梅子望林而止渴,木瓜呼名而缓筋,此无情而有情也。昆虫草木果知觉耶?人之与物果感通耶?气耶,理耶,孰居解耶? 文胜而周衰,清谈而晋败,道学盛而宋亡国,无实也。拘儒不可与谈玄,腐儒不可与论道。 天本明,云蔽之;心本明,欲蔽之。云散欲消,天心同澈;云锢欲钳,天心同闭。 五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此心性之学也。性统于心,故达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谓即本相而寻面目也。其曰:“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非心之虚乎?”又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非心之实乎?”其学可谓体用合一者也。 毙,从敝从死也鷩,禽之美者,人烹之;鳖介之美者,人庖之;币,货之美者,人贪之。物各以其美。毙此字之所以从敝也,人心虽灵,溺于物则敝。故曰:“憋至于眼目手足皆有敝。”故曰瞥,曰挲,曰蹩。 夏禹受禅而迅风偃木,恶其忘父之仇也。周成受谗而大风拔木,警其忘父之恩也。风木同象,父子一体,感则相生,逆则相仆。 以热攻热,药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则生,不善用则死。 大衍之数,五十虚其一,以象太极之无为也。人之脐其百,窍之太极乎?圣人虚一策以成化,至人虚一窍以养生。 有一乡一国,天下之量斯能受?一乡一国,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圣人孰不愿学也?貌不为圣人而心为圣人,善学也。貌圣人而心盗跖者,其今之道学之士乎? 天地之气,乱于春秋之世,而正于孔子之身。 以色曰妒,以才曰忌。吾闻仓庚可以止妒矣。欲止忌者又何物哉?嗟乎!不烹麟凤以食之,其忌不止也。 忍大师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归。”庄周曰:“生浮死休。”知其为大事,则人固不可轻于生死、而忽之;知其为寄归浮休,则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感之。如是可为了死生者。 螽斯春黍虽不足以济饥,而惰农愧矣;莎鸡促织虽不足以济寒,而懒妇惊矣;丹鸟挟火虽不足以济昏,而暗行惧矣。呜呼!其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玉笑零音》 (明)田艺衡 撰
玉笑零音 (明)田艺衡 撰 鹏运扶摇,不知游于天外。虱逃缝絮,不求出乎裈中。居化有宜,适真各得。 华渚流虹,虹非淫气;有穷射日,日岂阳精? 柱梁衣绣,而士寒咎犯,切中晋文之病;鼠壤余,而妹弃成绮,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为朽骨。神超者,以心为死灰。魄玄合者,以神为碍影。 神龙无孵卵,灵凤无孽雏。白狗不能产驺虞,黄狼不解天禄。 御寇好游,壶丘晓之以内观,宋经好游,孟氏语之以尊德,德尊则高而俯物,观内则明而烛人。酷刑为栉,则虮落黔黎,巧谮为钩,则鱼馁臣妾。故圣王栉之以礼,梳之以乐,钓之以义,网之以仁。上善若水,有时而作恶。贞心如石,有时而自开,是以怒动情澜,喜开欲窦。 诗人以素餐为讥,商君以荒饱为惧。 使勋华而为巢许,则丹商之恶不彰;使癸辛而为舆台,则禹汤之泽不斩。 雷无偏击,日无私烛。使编首而击之,则丰隆亦亵矣。推户而烛之,则义和其劳乎。击因邪召,烛以虚来。虚纳天光,邪其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周公封,而成王赐以天子之乐。弃天下尚为敝屣,假礼乐岂为虚文。生前名器或惜繁缨,死后功勋何难隧道。 心如天运谓之勤,心如地宁谓之慎。天匪勤则不能广运,地匪慎则不能久持。乾之自强,天心也。坤之厚载,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万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轻千乘之国。 阳鱎迎吏,宓子为之长挥。猛狗龁人,韩菲因之并叹。 景阳入并丽华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崖山踏海白鹇从,丞相犹存衍义进。君臣两失,禽色同荒。士苟洁心,无假浴于江海;女能饬体,何必竞其黛朱! 观文未及李生叹,愈老不休韩子悲。 刘累豢夏后之龙,孔甲醢鳞而龙游。孟亏驯虞氏之凤,夏民食卵而凤翔。 五府灵而中天之台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轩乘鹤,卫国谓之不君,以车载猃,周家名为贤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国。男服女服,何晏丧躯。 子云注情于绵竹,非杨庄无以上宣。相如立誉于子虚,非得意莫能自荐。 师开鼓琴,以东方西方之声,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律,以南风北风之辨,而测胜负之军。 女乐归而鲁削,巫音作而楚衰,汉饰伎以祭郊,唐藉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鲁叟悔徒思。惟克乃作圣,非学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葬之号,孝子不瘗其亲。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晋景公素缟哭之而水流。海潮击岸,百里为墟,吴越王强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鲧之智,不及于辇夫之言。而神禹之功,仅等乎铁箭之力。 鲍鱼小鲜,吕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恶菜,邢峙不进于储君。为传者,贵谨其几微。养德者,在慎其饮食。 师寒,而楚子拊之,三军暖如挟纩。兵渴,而曹操谲之,万众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实沉一台,非郑侨之博物不能言。龙见绛郊,非蔡墨之明占莫能御。虽禀生知之质,亦资好学之功。 隼虽鸷,不能以攫凤。虎虽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吏径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缓;三代以下由支径,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职也,今之业耕者,毁其锄犁,而诲其子以盗。织妇之事也,今之业织者,弃其机杼,而诲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织也,得饱暖。而今之耕织也,饥寒因之矣!耕织反不若淫盗。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而袜系解,自结之,而弗役其所与处,君道也。武王伐纣,而袜系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结,臣道也。周之君臣,两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将自结邪,臣将结之邪,一举足而见之矣! 杨朱泣岐路,阮籍泣穷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达。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殷已悫,吾从周然则文果胜悫矣乎!悫悲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庄纳伍胥之谏,而罢淫乐。齐威悟淳于之讽,而行诛赏。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贵信贤而改过也,名之曰庄威,不亦宜乎。 龙负夏禹之艇,卒治水而窆衣。蛇绕卫君之轮,遂投殿而伏剑。 阳,君道也,故尊而难对。阴,臣道也,故卑而喜应。九畴之凶,生于对奇也。八卦之吉,生于应偶也。风行天上,动万物者,莫疾乎风。水行地中,润万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择居,死者之择穴,皆莫离乎风水也。 治世不能无祠淫,正人未尝有淫祀。 潮汐之盛缩,因月之盈虚,古语如是,谁则验之?吾观于鱼脑之光减而信之矣!盖鱼虾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阴气之以类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无盐丑女也,虽丑而有益于国;庄列之文,西施美妇也,虽美而裨于世。 文胜而周衰,清谈而晋败,道学盛而宋亡,国无实也。 拘儒不可与谈玄,腐儒不可与论道。 鳌戴山而水居,蚁负粒而陆游;大小之乐,均也。蛇委腹而缓步,蚿百足而疾行,有无之势,一也。 孰重孰轻,孰多孰寡,孰劳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云蔽之。心本明,欲蔽之。云散欲消,天心同澈。云锢欲钳,天心同闭。 鸜鹆之勇能夺巢,终贻窃位之耻。蛣蜣之智能转丸,卒蒙秽饱之羞。泰伯逃荆,夷齐采薇,丑此故也。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圣人见道不远人,故曰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至人见道不外心,故曰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人即心也,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择木。兽之走也,挺以择荫。人之处也,审以择居。翔以择木,可以远矰弋。挺以择荫,可以远陷穿。审以择居,可以远刑辟。 恶土虽善,种不生。善土虽恶,种不死。良农择地而种,君子择人而施。 智者之纳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谏也,如以水泼镕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见其顺受矣。以水泼乎镕金,吾见其腾沸矣。非水之异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辞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有千里之马,而无千里之御,不能独驰也。有千里之御,而无千里之刍豢,不能久良也。善其刍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骐骥也。 忍大师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归。庄周曰,生浮死休。知其为大事,则人固不可轻于生死而忽之,知其为寄归浮休,则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为了死生者。 螽斯春黍,虽不足以济饥,而惰农愧矣。莎鸡促织,虽不足以济寒,而懒妇惊矣。丹乌挟火,虽不足以济昏,而暗行惧矣。呜呼!其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沉檀之木,不适用于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则,物有不同,时有所宜也。 虎豹驱羊,孰不怜。豺狼驱民,熟能愍? 罪春秋于当时,仲尼不得已也。期子云于后世,杨雄其如何哉? 虽有金钟,击以金梃,其声必裂。虽有仁主,辅以仁臣,其治必弱。扣金钟必以木槌。佐仁主必以义士。权会庄诵易卦,而却乘驴前后之鬼。徐份诡诵孝经,而愈陵久危笃之疾(会北齐人,份陈人)。 猛虎之势,奋于一朴。三军之气,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为麋鹿之解角。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为小人之易心。绳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锦食鲜,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粝,聊可以卒岁。 句践铸金于少伯,君子谓之貌臣。贯休铸金于贾岛,君子谓之心师。 王右军之书,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诗,五十外始学。 阮籍之放,见称于司马。稽康之和,致忤于钟会。晋公之度,征西之祸,于此见之矣。 萝茑依松林,可以延百寻。青蝇附骥尾,可以致千里。其为依附则得矣,而如仰高居后,何哉! 尧舜之爱身,甚于爱天下,故让天下于许由务光而不吝,许由务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尧舜之爱天下,不如爱子,故不以天下与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让天下与舜禹而不争,不贤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苍梧会稽之祸,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国,而死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则为之贪位慕禄。屈原甘于九死,在今人则为之病狂丧心。 吴起吮一人之疽,而邻敌却。假烦裹一人之疮,而西羌平。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国安。私恩小惠,三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为将之道何如? 晋文公二竖,入于膏肓,扁鹊识之。秦孝王崔妃,入于灵府,许智庄识之。非察其疾也,乃诊其(心也)。 栾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敛广汉实切师、生之义。 良匠之目,无材弗良。圣主之目,无臣弗圣。非材之尽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尽圣也,内外各有所使也。 鸡鸷雄埘,犬猛专牢,强弱之不敌也。蚁勇兼垤,蜂策攻窠,众寡之相凌也。据势以猎,冯力以角,其诸春秋战国之君乎。 孔子以死丧之道为难言,重阴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气为难言,重阳道也。然则终不可言与,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谷种,长生之仁。死生不测,造化之神。 防细民之口易,防处士之口难。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难。此七国所以惧横议,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齿焚,犀以角毙,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诛,蛇以珠剖髦,断尾以缨,狐分腋以白,龟钻甲以灵,麝噬脐以香。故曰禽兽无辜,怀宝其害。匹夫何辜,怀壁其罪。嗟夫!罪在怀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独何与? 地以海为肾,故水咸。人以肾为海,故溺咸。 以热攻热,药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则生,不善用则死。 若纲在网,掣绳者君。如锥处囊,脱颖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人之初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微言绝耳,颜远叹别于欧阳。鄙吝萌心,仲举思见乎黄叔。 君子之异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阅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逍遥子之大葬也。 西伯泽及枯骼,而大老双归。燕昭价重死骨,而骏马三至。 白驹过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飞鸟过日,张翰愁思乎瀛海。 大禹入裸国而不衣,秦伯适荆蛮而披发。父母之遗体,有时而自残,衣冠之盛仪,因地而或废。 仲尼击槁而歌焱风,仁可以充饥也。曾参曳履而歌商颂,义可以御寒也。 分人以道谓之神,分人以德谓之圣,分人以功谓之公,分人以利谓之私。 田子见玉食,蹙然曰,弗饥,斯可矣。见锦衣,颦然曰,弗寒,斯可矣。见华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尔食,而玉尔仪。毋锦尔衣,而锦尔心。毋华尔屋,而华尔德。惟仪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锦,以文天下。惟德之华,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结袜而重廷尉。汲黯以长揖而重将军。 吴雄不择封葬,而三世廷尉。赵兴故犯妖禁,而三叶司隶。陈伯敬终不言死,而年老见杀。 学非诵说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饰之具也,实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则神矣! 有一乡一国天下之量,斯能受一乡一国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妇析紫荆之干以图分。刘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以雏以求异。故齐家者,先刑其室,正内者,必绝其私。 仓庚为炙,可止妒妇之心。凤凰为羹,难化忌士之口。 太公诛狂獝华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贤。放勋容驩鲧共苗,重华矫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画生鲻而执白獭,放挫啼,悬死鼠而钓大雕。画鲻其冠裳乎,悬鼠其爵禄乎,呜呼悲夫!孔子历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历流沙八十一国,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倚墙之木盗之桥,倚床之仆奸之招。 周旦作金滕以祈天命,君子以为咒诅之媒。夏禹铸鼎象以辟神奸,后世遂有厌镇之术。 亡国之社,上屋而下柴,绝于天地也。败家之子,覆祀而灭嗣,绝于祖宗也。 心灵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禄役其心。心虚匪气,故阴阳不能运,而人反以喜怒运其气。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动也。尽心者虚,存心者灵。 祭葬厚而奉养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顺过而弼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颜,忠之大。琴瑟合调,夫妇之所以谐音。埙篪一节,兄弟之所以同气。鼋鸣而鳖应,兔死则狐悲。 人之为学,四书其门墙也,五经其堂奥也,子史其廊庑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广,学不可以不博。举业锢而居隘,语录倡而学荒。 有子如龙虎,不须作马牛;有子如豚犬,何须作马牛! 涪水杂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剑精。石城杂南冷,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师元帝,为周围尚谈老子之旨。海岛宋君,为元逐犹讲大学之章。腐臣朽主,自取灭亡。神谟圣训,何裨解禳。 天地施恩于万物,而不望万物之报,吾是以知天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孙,而不望子孙之报,吾是以知父母之大。天为严父,地为慈母。少极吾宗,太极祖,巍巍乎其功德,荡荡乎其难名哉!腐鼠堕而虞氏亡,猰狗逐而华臣走。孽虽由于自作,衅实起于不虞。 欲治疑狱,觟■〈角虎〉解触,咎繇碌碌。若济大师,仓光实危,尚父嗤嗤(光一作兕)。 败岁皆莩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梦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儿舞女之将军。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难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积,不羞金之不积;善贵者,耻德之不伙,不耻禄之不伙。德以聚金,则满不扑,德以居禄,则鼎不颠。 苏子瞻作杀鸡之疏,非吾儒之仁。张乘崖转到羊之经,乃异端之义。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贤者,必胥大位。无良材,则良匠不足以成器。无大位,则大贤不足以成治。临厕而惰容,非颜闵之德。膺刃而回虑,非关比之忠。 君子寝义而梦荣,小人寝利而梦辱。是故寝薄冰者,梦溺;寝积薪者,梦焚。 乾盖西旋,故二曜转运;坤舆东转,故百谷马奔。暮没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则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则水亦不耗。 民五百里之名,士无千里之名,仲尼所以来凤狗之诮。民无百里之友,士无千里之友,林宗所以丛党锢之灾。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东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黾当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箫管,道贲之声,实有契于定慧。 诗因鼓吹发,桓玄耳入而心通。笔以鼓吹神,张旭得心而应手。 珠虽泐不失为宝,莠虽乔不失为草。宁为回天,母为踱老。 江河若决,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既开,周公不能复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时。 日月不以阴霾而改其升沉。圣贤不以昏乱而变其出处。有常度万物仰,有常德万民望。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为阱,则士游祥麟。以德为笼,则士来瑞凤。以功为罟,则士投猛虎。以利为薮,则士奔狂狗。梓庆鐻成而疑鬼,灵芸针妙而惊神。圣道散于游艺,天巧丧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杀身,小人也。被发箕子昌,驾坐灌夫亡。接与陆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日闲与卫,何难乎良马之逐。不离辎重,岂忧乎终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备,丧握本于持轻。 月不暇照,云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轮灌陇。 笑之频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铸万物,圣人鼓之天蕴至文,圣人诂之。铸非鼓,则器将监。蕴非诂,则文不宣。 附录: 玉笑零音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田艺衡撰是书皆采取新竒故事纬以俪语凡一百二十八条其中如以尧舜之让天下爲爱身不与朱均以天下爲爱子舜禹之受天下爲不知害铸鼎爲鎭厌之术金縢爲诅咒之媒皆纰缪之甚者已编入所着留靑日札中此乃其初出别行之本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