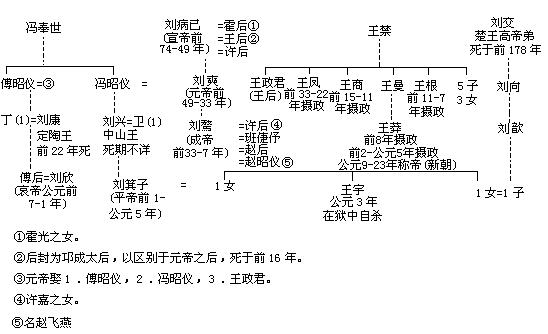|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未来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时,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67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理的大臣们的批评。[1]
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后来王莽继承了改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和哀帝(公元前7—前1年)几朝相比,甚至进一步地发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国内政治
当时重新进行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京城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由翼奉的建议引起的,翼丰是萧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个根据阴阳的循环来解释王朝历史的阴阳家。[2] 他提出皇帝和政府的所在地应移到洛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他希望断绝汉朝与长安的关系,因为那里是暴力和战斗的场所;此外,在王朝初建和武帝的扩张挥霍时期,它又曾被用作权力基地。但是洛阳却引起人们对周代诸王的道义美德和俭朴政策的追忆。翼奉建议的论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他得到皇帝的赞赏而被召见了一次;但他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个问题直到公元12年才再次提出。在此期间,长安继续得到充实。皇帝仍在收集工场制作的铜器以装饰皇宫。有的珍宝被送往长安之西的上林苑,那里有猎场、供游猎用的馆舍、御苑和各地送来的珍奇动物;上林苑在武帝时期已大加扩充。
元帝及以后的几朝恢复了几个王国,它们一般是小国,有的存在的时期不长。其中的两国(楚,于公元前49年重立;广陵,于公元前47年重立)维持到西汉结束之时;其他诸国有:清河(公元前47—前43年)、济阳(公元前41—前34年)、山阳(公元前33—前25年;原为昌邑国)和广德(公元前19—前17年)[3] 。有一个王国(河间)在公元前38至前32年期间被当作郡来治理。由于与王朝的瓜葛,定陶、中山和信都三国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定陶于公元前25年复国,存在到公元前5年;在这期间它的一个王刘欣已被晋升为太子,后来成为哀帝(公元前7年—前1年)。中山从公元前42至前29年又成为国;公元前23年以前回复为郡,前23年被重新批准为国;其王刘箕子在公元前1年继哀帝登上皇位,成为平帝。信都国从公元前37年维持到前23年,从公元前5年起又成为国;在这个间歇期中(公元前16年),王莽曾被封为信都侯。
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数授予诸王之子,总数达100个;与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个,赐给外戚的侯为25个。
在前汉时期,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至少有一个政治家因宦官与之为敌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年)两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对他们的立场。
到那时为止,曾任秦帝国大臣的赵高是宦官控制帝国命运的唯一明显的例子。[4] 其后,少数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受宫刑的人仍设法在汉代留下了他们的名声:这些人包括司马迁,他因在李陵身处逆境时赞扬李的功绩和为李的行为辩护而付出了代价;李延年,他是武帝的一个妃子之兄,因他在乐府的活动而知名;许广汉,宣帝的遇害皇后之父,他因偶犯的一个小过失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5] 可能在武帝统治之前和之后,宦官都在帝国的朝廷上担任较低的职位;当尚书的官署日趋重要时,他们很可能在署内任职。[6]
最早得到晋升而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的决定产生相当影响的宦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显。他们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萧望之的强烈批评,他反对设置宦官,让那些被阉割的人身处君侧。然而,当宦官的势力强大得使人感到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时,作为他们敌视的结果,萧望之在公元前46年被迫自杀。[7] 匡衡就是那些痛恨宦官而被石显及其同伙指控的人之一。到公元前33年,弘恭和石显都死去,其他宦官都没有取得足够显赫的地位以接替他们去控制皇宫;公元前29年,由宦官任职的专门机构(中书)被撤销。
有若干措施证明政府有重建公正的行政和减轻以前规定的严厉惩罚之意。这类措施涉及大赦令、司法程序和以金代罚的规定。
在公元前48至前7年期间,朝廷共颁布了18次大赦令;虽然大赦的次数并不明显地多于以往,但颁布大赦的诏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们表达了一种观点,即严厉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们暗示犯罪的增加是征重税或未能保证行政清廉的结果。除了公元前134年与大赦令一起颁布的一道诏令外,以往在这些情况下是不谈这类意见的。此外,公元前47、46和32年的几次大赦令郑重地表示了皇帝要弥补因他的无能而引起的宇宙万物运行失调的企图,这种失调通过上天的警告已经表现了出来。朝廷坚决地认为,大赦是及时地注意这些警告和作出补救的一种手段。[8] 几乎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减轻法律规定的某些严刑(在公元前47和44年)。在公元前34年,它又指示简化和缩短诉讼程序;长期的诉讼严重地扰乱了黎民的生活。[9]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97年,50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10] 这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约在公元前62年,萧望之已经坚决反对把这一制度稍加改变而予以实施的建议。有人曾经提出,定罪服刑的罪犯可以参加镇压西羌叛乱者的征剿,从而免除进一步的惩处。萧望之成功地阻止朝廷采纳这项建议。[11] 在贡禹担任御史大夫后不久(公元前44年),他就时弊向皇帝作长篇陈述时提起了折刑之事;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降低公众生活的〔道德〕标准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他的反对意见是否被采纳,他的建议是否被实施。[12]
节约
改造派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为宫中的挥霍浪费现象而感到痛心;它消耗了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资源,浪费了本来应该专门用于谷、麻和蚕丝生产的劳动。元帝登基后不久,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减奢侈用品,俭朴蔚然成风。公元前47年,提供车马以供皇帝使用的专门机构被撤消,同时撤消的还有专用的某些湖泊和林苑;次年,宫中禁军的编制被缩小,官员们奉命削减开支;公元前44年,即暂时取消国家盐铁专卖的那一年,在皇帝的宴会和使用交通工具方面都采取了节省措施。[13] 为娱乐而布置的一些比赛停止举行;很少使用的一些狩猎庄园被关闭;原来在中国东部设立的供应宫装的官署也被撤消。公元前44年的另一个措施表明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仅仅为节约而急于紧缩开支;他们对国家资源的使用还怀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受博士官训导的学生人数有名额限制。在实施紧缩开支的措施的同时,朝廷取消了对学生人数的限制,以期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人担任公职。但由于这一变化增加的费用,在公元前41年,学生人数又有了名额限额。[14]
有一个进一步的节约措施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它产生于财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它是宣帝朝的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的继续。早在公元前70年,乐府已奉命削减其正式编制;公元前48年朝廷又颁布了同样的命令;15年后乐府又奉命停止某些比较铺张的做法;诸如提供国祭仪式中的女歌诵团。最后,在公元前7年,乐府被撤消。在那时,它共有829名精通音律的人充当歌诵者和演奏者。一半以上的人被直接遣退,其余的人被调到其他机构;但朝廷仍能为朝觐组织一个有128名乐师的乐队,为宗教祭祀组织62名演奏者。[15]
乐府有许多精于音律的人任职,尤其是在下达紧缩编制命令之前。但是撤消乐府的记载着重叙述的是乐府已被败坏了的职能而不是节约钱财的需要。到乐府结束之时,它已与演奏容易引起情欲和刺激放荡行为的靡靡之音联系了起来。在几个世纪之前,孔子已经不赞成这类音乐,所以改造派政治家们设法压制为国家演奏这类音乐的组织,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它会对世风产生有害的影响。
政府中一名可以代表新潮流的官员为召信臣,他生于华中,他学术上的丰硕成果使他能在朝廷取得一定的地位。[16] 他先任一个县的县令,后任南阳郡的郡守,在任郡守时,他极力使百姓富足起来。他亲自在田地劳动,给人们树立勤奋的良好榜样,并不知疲劳地视察供水情况和改善灌溉设施。这些措施使郡内的生产大为提高,于是仓廪充实。郡守还成功地说服百姓为公平分配水的使用达成协议。他阻止了立界石争产权的争端的爆发,并大力提倡节约。对那些喜欢过懒散奢侈生活而不愿在田地劳动的下属官员的家族,他威胁要提出诉讼;他赢得辖区百姓衷心的支持,那里的人口翻了一番。
由于这些成就,召信臣得到了应有的奖励;他先被提升为河南郡郡守,公元前33年又升任少府。就在任少府期间,他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一级节约开支的建议。他提出应中断维修皇宫的那些很少使用的建筑物;乐府应该撤消;戏班和正规的宫内禁军的武器装备应大大地减少;他极力主张,用于促成某些作物和蔬菜在非种植季节生长的燃料开支是不合理的。还可以补充的是,召信臣幸运地是一位在职时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有成就的高级官员。
除了削减开支的尝试外,在新朝伊始之时元帝的顾问还提出了其他的旨在抵消武帝时期新派政治家们的过激政策的措施。改革的主要拥护者是公元前44年任御史大夫的贡禹。他强烈地反对雇佣国家征募的劳工采矿或铸币;他断定用于这类事业的劳动日多达10万个以上,他反对让农民承担生产矿工和工人所需的粮食和布的义务。
贡禹竟然成功地使国家的盐铁专卖在公元前44年取消了。但不久收入的减少越来越严重,专卖事业又在公元前41年恢复。[17] 贡禹还关闭了用作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粮仓。讲求实际的耿寿昌急于尽量减少运粮的劳动力,于公元前54年又建立了粮仓。[18]
贡禹又提出一个建议,但它甚至没有被短期采纳;这个建议就是以一种货币前的经济来代替货币经济。他争辩说,爱财是万恶之源;它吸引人们脱离田地的生产性劳动而去从事工商,工商可以不花什么劳动而取得厚利。钱的使用可以使富者积聚财富;富者利用财富纵情享乐和进一步追逐利润,因为放债可以轻易地取得二成之利。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的诱惑,使他们放弃土地去寻求似乎可以致富的一条直道,这几乎是无法压制的,因为他们被钱财弄得神情恍惚。但如果他们不能发迹,其下场将是一贫如洗,出路只有当盗匪。
贡禹提出关闭官办的铸币厂;征收粮食或织物作为岁入;完全以实物支付官俸,以取代官员已经习惯的钱和粮合计的月俸。贡禹的论点也许是讲得通的,但由于货币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它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如果高级文官收到大量粮食作为他们的官俸,他们就会遇到处理粮食的困难,所以很难指望他们会支持贡禹的建议。
就在前汉末年,一个甚至更为激进的措施被提出,但同样没有成功。这个建议是在公元前7年任大司马的师丹的鼓动下出笼的。象贡禹那样,他深感贫富之间严重的悬殊;他又象董仲舒那样,寻求通过土地的再分配来缓解苦难。他就土地的规模和可以拥有的奴隶人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额,其大小和多少依社会地位(拥有的爵位,或是侯)而定。[19] 建议被提交讨论,并原则上被采纳;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如傅后和丁后的外戚及哀帝的宠臣董贤,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这个建议未付诸实施。就在此时(公元前7年),政府为了减少支出,颁布了与公元前47至前44年所采纳的措施相类似的节约措施。
自从公元前109年整修黄河的堤坝以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动。在公元前95至前66年期间,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经挖成,以减缓大水顺流而下的沉重压力;但政府对疏浚或维修的必要性还没有充分注意,于是在公元前39年和29年发生了大决口。公元前30年,大雨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造成了洪水,长安城内惊慌失措,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20] 公元前29年,洪水为灾的责任被归之于御史大夫尹忠。他成了时弊的替罪羊,因身居高官,只能自杀谢罪。
以后,大司农负责此事;通过迅速有效的行动,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险的形势。他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救灾行动,使用了500条船只以撤走受威胁地区的居民。为了把洪流疏导至支渠以防止进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坝。经过36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劳工,这个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号“河平”(公元前28—前25年)以示庆祝。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威胁,下一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7年。[21]
幸运的是,《汉书》收有公元1至2年帝国形势的基本情况的概要。它列出了当时全部的行政单位,同时还有为征税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记报表。[22] 在最后几次调整之后,公元1至2年的帝国包括83个郡和20个王国,它们据称共有1577个诸如县和侯的下属单位。从各个郡和王国所列数字得出的总人口登记数合计为12366470户,或57671400口。
县及其市镇的材料较少,因为所收的这类数字只有10例。未提选列它们的原因,但可能它们说明了帝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它们难以引导我们了解当时可能存在的其他1500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例如京师及其所在的县的数字为80800户,或246200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区的居民约超过8万。[23]
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人口高度集中在丰产的黄淮流域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见地图10)。《汉书》中提供的可耕地规模有些难以解释;但情况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产可充分供应全民的粮和麻(衣服的主要原料)。最后这一卷附有一个政府设立以管理各类生产——如盐、铁、果品和织物——的所有专使的注。[24]
宗教问题
以前的几个皇帝竭力保持对五帝的应有的祭祀仪式,认为他们守护着王朝的命运。[25] 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亲自参加祭祀古代神祗,早在秦帝国以前很久,人们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在时新派的鼎盛时期,他曾经主持对其他的神——后土和太一——的祭祀。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继续举行这类仪式;他的继承者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在公元前47至前37年期间至少参加了11次祭祀,使仪式更为隆重。但是,变化正在发生。
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坛或由方士祭祀的神坛被取消。[26] 但是远为激进的变化涉及继续举行重大国祭的地址和在那里祭祀的方式,尤其涉及了祭祀的对象。这个变化主要是匡衡有说服力的陈述造成的,他推动变化,以之作为对古制的恢复,古制已经腐败,需要清理。他争辩说,象雍、甘泉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祀。[27] 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205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31年起,汉成帝在长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14、7和4这几年,宗教仪式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5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26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目的而建庙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年的一道诏令,它命令在京师和地方建庙纪念高帝。[28] 惠帝在登基时曾亲临一座宗庙,公元前166年的一道诏令还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29] 到元帝时,维持宗庙仪式的费用连同每日供品的固定数额增加到了惊人的程度。各地167个宗庙和长安176个祭祀地需要的费用的数字,引述得相当精确。因此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这些数字似乎引自经过适当审定的帐目。每年供应的斋饭为24455顿;有45129名士兵守卫宗庙;雇有12147名僧侣、厨师和乐师,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负责献祭的牲畜。[30]
在推行其他节约措施之时,重新审议这些仪式是不足为奇的。约到公元前40年,朝廷已经进行了大量削减。约200个宗庙的仪式中断了;但为纪念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庙的仪式则被挑出来予以保留,因为这几位皇帝被认为应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年元帝患病时,所有庙宇的祭祀被恢复;次年当知道这些求福活动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时,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年,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继承者成帝能得到一个太子时,仪式又被恢复。公元前7年,53名官员再次呼吁减少宗庙的数字,这一次在应享受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单中增列了宣帝。[31] 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期间,王莽重申了保留庙宇的原则,以便举行那些应该祭祀的活动。
另一个渊源于改造派原则的变化同样与宗教仪式、对人民的管制和国家的支出有关。秦始皇开了建造宏伟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先例;虽然据说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曾表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很可能汉代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们的地位用奢侈品装饰其陵墓。[32] 除了建墓和提供珠玉、装饰品及供应的费用外,政府有时还拨给庄园,以提供用于维修陵地的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此外,政府有时下令强制迁移人口,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照管陵墓和为它们服务。为了响应这类命令,有时富户或有名望之家的成员被强制迁移。
从高帝起,象这样的迁移发生了七次,都与在长安西面和北面准备某个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关系。[33] 这几次迁移可能被政治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认为这是把有权势的家族迁离它们已建为权力基地的故土的良机。一直到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期,这种安排都得到了支持,公元前55至51年任丞相的黄霸就是一个实例,他本人就为此目的而被迁移。[34] 但是在元帝、成帝、哀帝或平帝这几朝,史籍只记载了一次出于这一目的的迁移。公元前40年的一道诏令说明了朝廷的意愿,容许黎民留在其长期居住地,防止因强制迁移造成家庭分离而容易引起的不满。[35] 然而,如同国祭和祭祀列祖列宗的仪式那样,在成帝朝(公元前33—前7年)朝廷又一度恢复了更早的做法。成帝在公元前20年视察了为自己的陵墓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并且下令按惯例向那里迁移人口;但在公元前16年,迁移停止。[36] 几乎与此同时,刘向表示他强烈反对厚葬礼仪。[37] 公元前5年阴历六月,政府下令为准备丁后之墓而进行一次迁移,但在下一个月,它宣布将来它无意再采取这类行动。[38]
外交事务
在前汉的最后50年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不愿进行扩张,有时拒绝与潜在的敌人交锋。从积极方面看,中国总的说不再受到匈奴的挑衅,后者不够团结,难以巩固或加强其地位,或者对中国构成威胁。外国的重要权贵不时地访问长安,如成帝和哀帝两朝时的友好的龟兹王;公元前1年,乌孙的领袖(昆弥)之一与匈奴的一个单于一起来到汉廷。[39] 在此期间,中亚的移民定居地在都护的领导下仍得以维持下去;在公元23年以前有关于在职都护的记载。[40] 同时,朝廷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协调移民地工作和在紧急时刻给移民地提供军事援助。公元前48年,朝廷设了一个新职。在职的官员为校尉级,他将在原吐鲁番(车师)统治者拥有的领地上和这时易受匈奴侵入的领地上建立移民地;他将在这个地处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地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晚至公元16年,这个职务肯定还有人担任。[41]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急于避免进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年,海南岛的珠崖郡被放弃。原来设在海南的第二个郡已于公元前82年与珠崖合并;公元前46年撤郡之事是在当地爆发了叛乱和作出了在该岛保留中国的前哨将会过于劳民伤财的结论后发生的。[42] 四年后,西面的羌族诸部策划叛乱,当时中国正遭受饥馑之灾。在这些地区有丰富治安经验的冯奉世请求派军4万去镇压起义。但政府因需要保存实力而犹豫不决,只派他率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出征,兵力根本不足。象这样的虚假的节约不足以成事;元帝的政治家们最后被迫增派6万名士兵,冯奉世才得以恢复秩序。[43]
中国政府这几十年表现出缺乏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36年。[44] 当时,匈奴中最强大的领袖之一郅支对中国的政策不满;他对他的敌对单于呼韩邪所受到的友好接待心怀妒意,而他自己主动的表示则遭到了拒绝。郅支向粟特(康居)求援,以便报复;他希望通过诸如袭掠或俘获中国使节和攻击中国的盟友乌孙的行动,损害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发展下去,形势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交通线可以轻易地被切断;正是由于在当地的两名军官的主动行动,这个危险才得以避免。陈汤的地位在当时比较低。他完全自作主张地行事,发出了出兵进攻郅支所需的文书。结果,他得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他们一起战胜并杀死了郅支。
这两名将领以传统方式送呈被征服的为首敌人的首级向长安的上级报捷;他们完全预料得到的一场争吵随之发生。因为从表面看,他们犯的罪是严重的;它们颁发了一道自己无权颁发的诏书。只是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才使他们免受可怕的惩罚。政府无意向他们祝捷或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奖励;它也不愿意通过进一步的扩张去利用他们的胜利。反对以任何方式奖励他们的意见主要是匡衡提出的,只是由于刘向的坚持,朝廷最后才封甘延寿为侯,封陈汤为关内侯。甘延寿死后,匡衡乘机降低了陈汤的地位。
政府对它的两名最英勇的公仆的不公平待遇表明,它这时不愿投身于对外的冒险行动中去;对他们的任何奖励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它会鼓励其他人去显示其主动性,并把中国卷入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之中。30年前(公元前65年)当冯奉世提倡中国向中亚推进时,所采取的恰恰也是这种态度。[45]
另外的行动也产生于这种对外关系的观点。粟特最后起来反对郅支,甚至在陈汤决战时出兵帮助他。当有人提出应与粟特保持这种关系时,汉朝政府不赞成通过和亲进行全面结盟。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已在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与克什米尔(罽宾)建交,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断交。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3—前7年)有人提出重新建交,但未被采纳,理由是虽然克什米尔可以从这类交往中取得很多利益,它并不是真正想争取中国的友谊,而只是出于私利在追求物质利益。②
王朝的种种问题和皇位的继承
成帝是元帝和王政君之子,后者作为太后,在以后几十年决定王朝的命运时,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成帝出生时其父仍为太子,这个儿童已得到他祖父宣帝的宠爱。宣帝死后不久,他被指定为新帝的太子;公元前33年他登基时年19岁。[46]
在青年时代,据说成帝已经表现出他明显地爱好学习的习惯;根据一个传说,他已知道去领会尊重长辈的价值观念。[47] 关于他后来一变而纵情于酒色和靡靡之音之说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历史学家的偏见;因为《汉书》的作者是班家的成员,因此与皇帝曾经亲切地关怀——但也许结局不佳——的一个妇女有亲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偏见,关于成帝缺乏意志力或高贵的性格以及他纵情于轻薄的放荡行动的说法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郑声为腐败和放纵的象征,被责为淫荡之音,但在他的宫廷颇为流行;公元前20年以后,他开始养成在长安微服出游的习惯,以追逐诸如斗鸡等声色之乐。[48] 有人指出,正是由于他性格上的这种弱点,他父亲元帝曾想以傅妃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取代他为太子,但正是由于傅家对元帝施加了压力,又使元帝迟疑不决。
未来的成帝之能继续当太子,应归功于两名以改造派观点知名于世的政治家。一为匡衡,在成帝登基不久,他乘机向新君说教,教导他应以周代诸明君的言行为榜样;成帝之登基部分地是由于师丹之力,此人于公元前7年提出了限制财产的建议。[49] 没有证据证明成帝本人对当时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的看法,或者明显地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有任何影响。
成帝娶许嘉之女,许嘉是元帝之母的堂兄弟,因此是公元前71年成为霍家野心的牺牲品的那个许后的亲戚。成帝的配偶于公元前31年正式被立为后,但所生之子在婴儿时夭亡,这成了成帝及其继承人几朝发生混乱的潜在原因之一。根据传说所透露的严重的妒忌和残酷心理会使任何王室感到羞耻,所以必须再次提防历史学家可能带来的偏见。[50] 简而言之,成帝被一个出身低贱但以能歌善舞知名的少女的美色所迷,这些才能在此之前已使她有飞燕之称和在一个公主的府中有一席之地。赵飞燕和她的妹妹都得到成帝的宠幸,到公元前18年,她们指责许后行施巫术,成功地废黜了她。对潘妃也进行了同样的指控,但由于她天生的机智,她们未达到目的;她宁可退出宫廷的是非之地。晋升之路对赵氏姐妹及其家族敞开了。
赵飞燕在公元前16年正式被宣布为后,但她与她那在其他妃子中享有高贵地位的妹妹都不能生下子嗣。在以后四年,她们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成帝与一名宫女和另一名正式的妃子生下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婴儿被成帝下令处死,也可能他亲手处死,以防其他家族把赵氏姐妹从至尊的地位上搞掉。
在此期间,国家大事和十分重要的继承问题受到了其他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实力增强的王氏家族和通过与皇室联姻而青云直上的其他两个家族的影响。
成帝时,王氏家族采用了约50年前摆脱霍家的同样手法,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几乎让其成员实际上在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官署之一世袭任职。在元帝死去和升他的配偶为王太后之后不久,王太后的弟兄王凤担任大司马(公元前32年);因此他负责领导尚书和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他之后王家有四人依次任大司马;最后一人为王莽,他在公元前7年,即在成帝死前约四个月被任命。[51]
皇位继承的问题长期以来早就影响着政治家和那些追逐权力的人的心志,因为皇帝没有由公认的合法配偶生下的子嗣。[52] 当公元前8年出现这个问题时,有两名可能的候选人。一人是元帝的傅妃的孙子刘欣,因此是成帝的隔房侄子。刘欣之母来自丁家;他在公元前22年曾被指定为定陶王,当时他只有三岁;他的候选人资格得到赵妃(成帝的赵后之妹)和当时的大司马王根的支持。除孔光外,所有的主要大臣都提出请求,结果,在公元前8年3月20日他被宣布为太子;他从公元前7年5月至前1年8月正式在位,帝号哀帝。[53]
落选的刘兴自公元前23年以来是中山王。论亲戚关系,他是成帝的异母弟兄,因而比其中选的对手更近。他的母亲是元帝的冯妃,即曾在中亚有赫赫功绩的冯奉世之女。刘兴死于公元前8年9月,他的儿子刘箕子从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在位,帝号平帝。
对王家来说,哀帝朝是其命运遭受挫折的不吉利的间歇期。与赵、傅和丁几家新兴的暴发户相抗衡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当那几家平步青云时,王家却趋于衰微。哀帝继位不久,王莽失去了大司马的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傅家和丁家的人当了大官,或者被
表8 宣帝至平帝的皇位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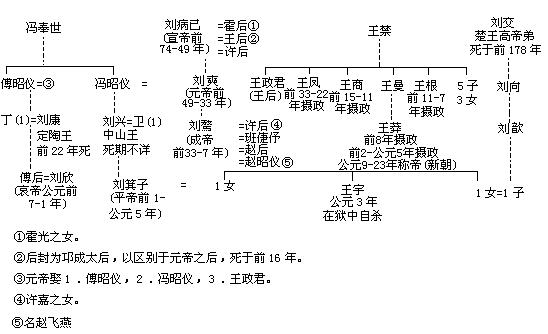
封为侯。后来,在哀帝死后(公元前1年),王莽策划东山再起,这时轮到成帝的赵太后遭受剥夺高贵称号和贬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势力,在这方面它们可能得到哀帝的鼓励,但它们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从傅喜起,它们的成员从公元前6年至前1年拥有大司马的官衔。但是傅喜被描述为一个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对他的几个亲戚要求取得显赫称号的活动。[54] 此外,改造派中坚定的核心人物在多次被认为是典型的争论中表达了反对新门第崛起的意见。师丹,这个曾经试图限制地产数量的坚定的改造派,坚决反对授予傅家的两个主要的女人尊贵的称号。孔光也坚定地反对给傅太后提供一座豪华的住所;除了所涉及的原则外,他希望阻止她对国家大事施加不应有的影响。[55]
历史学家称赞哀帝,说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样的个人力量进行统治。[56] 他心怀的这样的大志因他长期的病痛、外戚的势力和对娈童董贤的迷恋而未能实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崛起和受宠、他长期对皇帝的侍候(皇帝当时尚未满18岁)、他积累的巨大的资财自然会引起傅、丁两家的妒忌。[57] 但这两家的地位同两个太后分别在公元前5年和2年死去而大为削弱,董贤在年满21岁后不久任大司马。哀帝一度甚至提到把皇位让给他的宠幸的可能性;王莽的侄子之一阻止了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个提议的实现。[58]
哀帝死于公元前1年8月15日,未留下继承人;于是事态的发展迅速地有利于王家。曾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辈分和地位,她显然具有颁布诏令和为确保继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权力,在这样做时,她可以宣称她在遵循公元前74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贤被罢官和降级,但他立刻自杀而不愿丢脸。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拥有领导尚书的全权。
他决定防止敌对的外戚家族再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很快出现了贬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赵太后和追夺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谥号之事;采取最后的这一行动之激烈,竟然亵渎了她们的坟墓。公元前7年落选的皇位候选人之子刘箕子被选为新帝平帝。当时他年九岁。50000439_0232_0[59]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实际上在行使权力;他把女儿嫁给新的幼帝,这样他的地位终于保险了。但公元6年随着平帝之死,形势激变。[60] 他的敌人马上散布说,他害死了平帝,但这个指控的真实性始终得不到证实。不管情况如何,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说明王莽为什么不可能犯这类罪行。汉代历史中以前的情况表明,国内处于最强大和最有权势的地位的人是作为幼帝的父母、保护人或摄政者的男人或妇女。哀帝死时王莽年45岁,立了幼帝并把女儿嫁给他,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将是自己的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不也可能更为有利了。平帝之死与他自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王莽不可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随之发生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他企图开创一种与他自己的计划同样有利的新形势的行动造成的。
平帝死于公元6年2月3日。[61] 此时元帝一支已经没有后裔,新皇必须从宣帝的一支中挑选。这些人共有5个王和48个侯,但都被否定而挑了一个两岁的幼儿刘婴。王太皇太后颁布一道正式诏令,任命王莽为摄政;它特别说明王莽受托的地位与着名的周公的地位相当,后者是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的推行利他主义的摄政。通过这些方式,为当时形势所履行的手续就完全正规了;在4月刘婴正式被指定为太子,三个月后王莽被授予摄皇帝的称号。[62]
从元帝时起,皇位的继承几次成为争论的题目。人们向皇帝以建议或进谏的形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采取了各种行动以使规定的手续生效;所实行的原则和作出的决定成了帝国政府传统中的重要先例。当元帝在考虑改变继承的世系时,改造派政治家匡衡坚持一个合法的皇后和她的儿子具有高于他人的权利,并且坚持必须把其他后妃及其后裔降到低于她(他)们应有的地位。[63] 后来当挑选成帝的继承人时,有人分别为成帝的异母弟兄和隔房侄子发表了对立的意见。双方都引经据典(这些是为指导正确的言行和礼仪而定的)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一次,孔光争辩说,作为具有优先权利的近亲,本人就是皇子的成帝异母弟兄应该继位。形成多数的对立的一方也能引用同样重要的权威经典作为他们观点的根据:弟兄之子相当于儿子;结果,隔房侄子被选中。[64]
平帝和刘婴是前汉时期未成年的人或幼儿在他人的保护和主持下登上皇位进行统治的最后的例子。为了立一个摄政,虽然可以引用周公这样一个过得硬的和明显的先例,但人们也没有忘记霍光在当摄政时也作出过卓越的功勋。如同在公元前74年那样,哀帝和平帝死时在没有正式指定的继位者的情况下太后也拥有典章上规定的权力。
最后,至少有一次,一名官员认为应该提出皇位职责的神圣性问题,以此来非难他的君主。此事发生在哀帝建议(也许是开玩笑)仿效远古的尧让位于舜这一被人颂扬的例子并把治国大权交给董贤之时。王莽的一个亲戚提醒年轻的哀帝,统治天下之大权来自高帝,并非某个皇帝私人所有:“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65]
世纪之末的风气
公元前33年成帝登基后的40年的特征是政治的不稳定和王朝摇摇欲坠。任人唯亲在宫廷中蔚然成风,国家最高职位的封赏只是出于随心所欲的兴致或是为了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受到世纪末日感的压制,感到王朝需要振兴力量;有的人怀念武帝朝汉帝国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的实力和风纪;许多人敏锐地注意到自然异数中的变化或灾难的征兆。公元前3年全国的黎民普遍尊奉西王母,这个崇拜得到了那些想通过宗教手段寻求超度的善男信女的支持。[66]
在政治方面,以朱博为代表的时新派态度在短时期脱颖而出。[67] 朱博出身寒微,没有当时许多担任公职的人受过学术薰陶的有利条件。他具有一个习武者的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艺修养的文官的观点。当他升任公职时,他设法把现实主义的精神输入行政实践之中,他认为施政受到约束,既已过时,又误入了歧途。他觉察到,治理中国不必着眼于传统,而必须注意当前天下的需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具有改造派心态的人,他们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灾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现象作为批评皇帝的手段。例如,从诸如水灾或一次日月蚀的现象可以觉察阴盛的状态,并且把它们解释为妇女在宫中或在议政会上为非作歹的呼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公元前29年发生的灾象的注意,当时(1月5日)的一次日蚀与当晚宫中感到的地动恰好巧合。这方面的专家,如杜钦和谷永,很快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批评当时政策的手段。[68]
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69] 并且因他对其下属坚持严格的纪律和保证他所辖部门的效率而赢得了名声。他升任御史大夫,然后在公元前5年阴历四月担任丞相;但到阴历八月,他被控谋反,被迫自杀。他的垮台部分地是由于时势,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对流行的生活观点不屑一顾,他反对其对手的方式似乎是愚蠢和轻率的。但对其他人想从意识形态方面搞一次王朝复兴的企图来说,他担任高官的短暂时期是引人注目的。
在成帝时,象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70] 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近期的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71] 许多人无疑地感到沮丧,这种思想在高层中深信不疑,于是公元前5年阴历六月的一道诏令宣布立刻采用新的年号。[72] 为此而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有几个含意。它不但指新时代的降临,而且还用了过去的年号“太初”二字,这是在时新派政府取得高度成就的公元前104年为同一目的而采用的。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皇帝仍受病魔的折磨,丞相朱博自尽而死。这些事件可以作为象征,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1] 《汉书》卷九,第2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99页以下);卷八二,第3376页;卷九八,第401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1、155、161页。
[2] 《汉书》卷七五,第3175页以下。
[3] 公元2年在立广世国和广宗国的同时恢复为国。
[4] 见第一章《秦的崩溃》。
[5] 《汉书》卷九七上,第3964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3、124、195页。
[6] 宦官担任尚书时称中书。关于尚书的重要性,见第8章《九卿》。
[7] 《汉书》卷七八,第3284、3292页。在正史评述中表达的这一观点由于对宦官的内在偏见而应作某些修正。关于石显和弘恭,见《汉书》卷九三,第372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3页。
[8] 关于公元前47、46和32年的几道诏令,例如,见《汉书》卷九,第281、283—284、30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8、311、376页)。关于完整的大赦令表,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7—168页。
[9] 《汉书》卷九,第29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34页)。
[10] 关于秦代的做法,见本书第9章《刑罚的种类》。关于公元前97年折罪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0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09页)。关于其他事例和有关原则的探讨,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5页以后。
[11] 《汉书》卷七八,第3275、3278页。
[12] 《汉书》卷七二,第3077页。
[13] 《汉书》卷九,第281、284—28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6、312、314页)。
[14] 《汉书》卷九,第285、29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5、324页)。
[15]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章。
[16] 《汉书》卷八九,第3641页以下。
[17] 《汉书》卷九,第29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4页);卷七二第3075页。
[18] 《汉书》卷八,第26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53页);卷二四上,第1141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5页)。
[19] 《汉书》卷十一,第3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页);卷二四上,第1142页《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0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以下。
[20]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页以下、190页以下。
[21] 《汉书》卷二九,第1688页以下。
[22] 见《汉书》卷二八所列每个国和郡的条目以及卷二八下第1639页的统计方面的概要。这两卷所列的数字不是全《地理志》各个行政单位的统计数的准确的总数。
[23] 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6),第115—117页;又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19页以下。
[24] 更详细的情况见第10章。关于人口计算及其准确性的研究,是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1947),第125—163页。虽然《汉书》中有一个声明,说人口计算指的是公元2年的数字,但它可能是根据前一年的登记数。《汉书》实际提供的人口总数为12233062户,即59594978口,与正文中提供的各郡各国所列数的合计数不一致。与此相似的情况是,所列的下属行政单位1587(或1578)个应该是1577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汉书》中关于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的产量数字是为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这类数字对全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25]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章。
[26] 《汉书》卷二五下,第1257页。雍城古址共有203个神坛,只留存15个。各地总共有683个神坛,留下了208个。
[27]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页。见本章《高帝最初的安排》。
[28] 《汉书》卷二,第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78页)。
[29] 《汉书》卷一下,第80页;卷四,第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5、第257页)。
[30] 《汉书》卷七三,第3115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9页以下。
[31] 《汉书》卷七三,第3125页以下。
[32] 关于秦始皇之墓,见第1章《秦的崩溃》。在写作本文时,对汉代诸帝陵墓的发掘尚未完成,但诸王,如死于公元前112年的中山王(其墓已在满城发现)的奢侈的埋葬,说明汉代诸帝的做法同样浪费。关于文帝的观点,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
[33] 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1968),第174页以后;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西安,1959),第65页以下。
[34] 《汉书》卷八九,第3627页;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第177页。
[35] 《汉书》卷七,第29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7页)。
[36] 《汉书》卷十,第32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1页)。关于其中一次迁移对历史学家班固的影响,见《汉书》卷一○○上,第4198页。
[37] 《汉书》卷三六,第1952页以下。
[38]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页)。
[39]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391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1、176页)。
[40] 都护之职最初在公元前60或59年设立,当时由郑吉担任。由于没有在职都护的完整名单,所以不能肯定在公元23年之前该职务是否连续地有人担任。除了公元前46至前36年、前28至前24年、前19至前12年和前10至前1年,我们已知道历年任职的官员姓名;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
[41] 这个职务称戊己校尉,有一个时期它又分为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和己是天干中的第5和第6字。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卷九六下,第392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3、189页);何四维之作,第79页注63。
[42] 《汉书》卷七,第223页;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310页)。
[43] 《汉书》卷七九,第3296页。关于数字的可靠性通常受到怀疑,见第1章附录3。
[44] 《汉书》卷七○,第3007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章。
[45] 《汉书》卷七九,第3294页;卷九六上,第3897页(何国维:《中国在中亚》,第141页)。
[46] 这一部分的主要史料见《汉书》卷十、九七下和九八。又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56页以下、366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0页以下、252页以下及264页以下。
[47] 《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3页以下)。
[48] 《汉书》卷二二,第1071页以后;卷十,第3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95页);卷二七下,第1368页;卷九七下,第3999页。
[49]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第3341页以下;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4页);卷八二,第3376页。
[50] 关于全部详情,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65页以下。
[51] 大司马之职先后由王凤(公元前33—前22年)、王音(前22—前15年)、王商(前15—前11年)、王根(前11—前7年)和王莽(前7年)担任。
[52] 《汉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9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4页以下。
[53] 《汉书》卷十一,第33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5页以下)。
[54] 《汉书》卷八二,第3380页以下。
[55] 《汉书》卷八一,第3356页;卷八六,第3505页。
[56] 《汉书》卷十一,第3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页)。
[57] 《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
[58]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59] 《汉书》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8页以下。
[60] 《汉书》卷十二,第36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85页);卷八四,第3426页。
[61]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以下)。
[62]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0—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21—225页)。
[63]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
[64] 《卷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
[65]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66]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98—101页。
[67]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68] 《汉书》卷六十,第2671页;卷八五,第3444页。
[69]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70]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24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78页。
[71] 《汉书》卷七五,第3192页。
[72]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9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